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彭刚忆何兆武
2021-05-31
(来源:新京报 2021年5月30日)
5月28日上午,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者、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在北京家中离世,享年99岁。
这位历经了近代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历史学者的人生,本身就与家国命运的起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他对历史哲学和历史规律的思考与译介,也与他的人生在历史航道中的方向密不可分。何兆武虽然以“旁观者”自居,但在不经意之间以自己的思考、写作与翻译,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他对康德、卢梭、柏克等人的译介中,我们在其中隐约可见他在历史风浪中的思考和感悟以及近代中国在历史上的坐标。
为了纪念何兆武先生,《新京报》采访了何兆武的弟子,清华大学副校长,历史学者彭刚。在彭刚的讲述中,这位沐浴着五四和启蒙余晖的历史学者的晚年的关怀依旧没有改变——人如何面对时代历史,又如何在其中获得自由和尊严。

彭刚与何兆武先生,摄于2011年。
他们这一代学者最为关切的
是国家民族的命运
新京报:能否请你简单谈谈何兆武一生的学术追求,在晚年他还在思考和关心哪些问题?
彭刚:我们如果看何先生的《上学记》,他自幼在北京长大,在他内心深处从少年时代起就似乎只有学术生涯这么一个选择。他在西南联大读本科、研究生,濡染观摩了那么多更前一辈的大学者,再加上自身的天赋和勤奋,他有着非常扎实的学术训练,完全具备了成为一个出色的大学者的潜质。但是他晚年经常在访谈和文章中感慨自己属于“报废的一代”。
有不少人问过我,何先生这么说是不是过于自谦了?因为大家都觉得何先生在著述和翻译方面声誉卓著,有着极高的成就。但是我想,何先生的性格真诚而平和,他的这种自我评价,也同样如此。一个人在年轻时候做好了从事学术工作的充足准备,但是在他三十多岁开始直到年近六旬这一段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在一个学者最有精力和创造力的年龄段,恰恰是碰上了政治运动频繁、学术发展停滞的时代。所谓“报废”,绝非自谦,在我看来满怀沉痛和无奈。
上世纪何先生从事学术工作主要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参加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写等研究工作,在侯先生的工作班子里,他主要参加了宋明理学一些部分和明清之际西学传入的研究工作,同时还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名著。另一个阶段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他主要的著述和翻译工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他翻译的西方经典著作中,仅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就有八种,还有相当多数量的如史学理论等方面的译作,绝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他对史学理论的深入而系统的译介和研究,也是在这个时期集中展开的。他在人生的暮年才能够集中全部精力从事学术工作。只不过由于他的学养和勤奋,在人们心目中的确是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和翻译家。
作为一位人文学者,何先生在晚年依旧关心的是当下这个时代,希望更深入地理解个体与国家、时代、命运之间的关系。何先生的百年人生经历了从北洋政府到新中国的各个发展阶段,由于《上学记》广为人知,人们更熟知西南联大对于他人生经历的重要性。我想,他们这一代学者最为关切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特别是人民在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如何才能幸福地、有尊严地生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能否处理好19世纪中叶以来就困扰着我们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他一直关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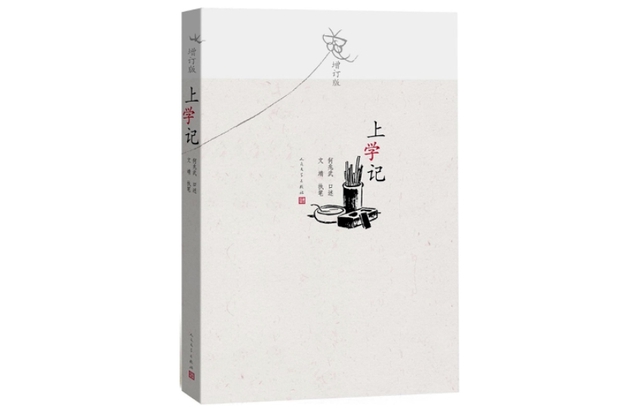
《上学记》(增订版),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3月版
新京报:何兆武的学术生涯中,不仅翻译引介了大量西方的人文著作,同时自己也著述颇丰,对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有着深刻的思考。何先生的翻译和著作体现了他怎样的追求?
彭刚:何先生在五、六十岁的时候,才有机会全力投入较为系统的学术工作。他翻译的著作很多是西方的经典名著,影响很大。今天他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我也看到很多人说:我们是读他的译著成长的。的确,卢梭、康德、帕斯卡、罗素等人著作的何先生译本,构成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阅读史上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和精神底色之一。
何先生的译作很多,质量也高,他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是因为他与这些思想家在精神上有着高度的契合。今天我还在想,何先生最爱康德、卢梭、帕斯卡尔。帕斯卡的一句话,也许是何先生自身的译文中他最喜欢的——“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何先生之所以翻译这些作品,我想,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些著作是西方近代文化中最具份量的作品,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著作和他的思想相契合,他想借这些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除了翻译工作之外,何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着值得我们重视的成就。前些天,何先生到了弥留的阶段,我陪伴在何先生的病床边的时候,还和他的公子(一位动物学家)说,除了学术翻译之外,何先生的研究工作是多方面的。比如他年轻时参与的侯外庐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侯先生在回忆录中对何先生写作的部分有着极高的评价。比如在我熟悉的史学理论方面,何先生不仅在国内筚路蓝缕,开拓了对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另外一方面,何先生本人阐发自己有关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思想的一些重要论文,从我作为专业研究者的角度来看,置之二十世纪世界史学理论领域最具原创性的作品之列,也是毫不逊色的。包括他对于科学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的很多论文,都非常值得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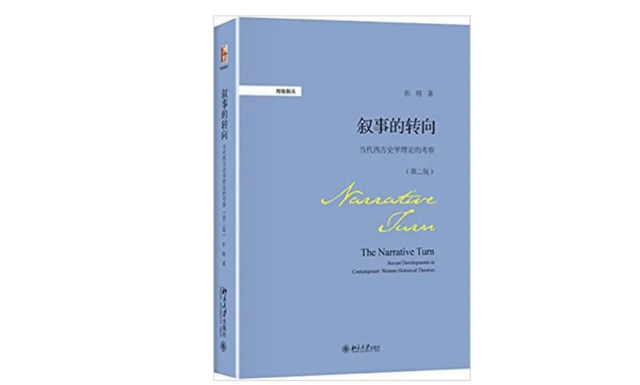
《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彭刚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版
他更多感兴趣的是历史背后的理论问题
新京报:何兆武在历史学的领域之外,对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着很高的兴趣。甚至在一篇访谈中主张人文学科的研究队伍招人的时候要多招一些了解自然科学的学者。你怎么看何先生对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兴趣?
彭刚:大哲学家康德在年轻的时候对于科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提出过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在科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即便是在高度关注科学研究的阶段,他也表现出自己的思维特点,那就是特别关注科学研究背后的哲学问题。
你看何先生的《上学记》就会发现,他在西南联大上学,听过很多人的课,包括钱穆、陈寅恪等大史家的课。可是何先生明确地说,他当然对于历史问题感兴趣,可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历史学家是如何来了解过去,从何种角度理解过去,是如何得出单靠史料未必能够得出的观点的。所以说他对历史学的兴趣,从年轻的时候就更多带有理论性的色彩。这一切理论的思考当然都会和哲学有着深刻的关联。另外,现代思想的特点,就在于它和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何先生以及他这一代的优秀学者,他们很重要的优点,就是特别地在意“通”,在意保持开放的胸襟和视野,使得自己的眼光和兴趣不受到学科界限的局限。
新京报:何兆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尤其关注西方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也提出了重建历史理性的想法。你如何评价何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
彭刚:何先生的学术工作,影响面更大的可能是他的翻译工作,毕竟,几代人文社科的学者,大学时代大概都免不了要读他的译作。另外他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也在不同领域有着各自影响。早年他在写作《中国思想通史》时候,关于朱熹、西学东渐、科学思想史的方面,都有一些独到的观点,是他毕生坚持和不断深化的。所以有时候我也会碰到这样的现象,有些学者知道何先生,是作为一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有人是把他作为一个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者,有人知道他是作为一个史学理论的研究者,他们并不知道何先生另外一些方面的工作。当然更多的人知道他,是他作为学术翻译家的身份。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单纯从何先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来说,何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重要的流派、问题和人物有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另外一方面,在翻译、研究、对话的同时,何先生又有一批重要的论文,比如《历史学两重性片论》《现实性、可能性与历史构图》等。这些论文集中阐发了他对史学理论的根本问题的考虑。在我个人看来,这些论文足可以放诸20世纪这一领域最精粹的文献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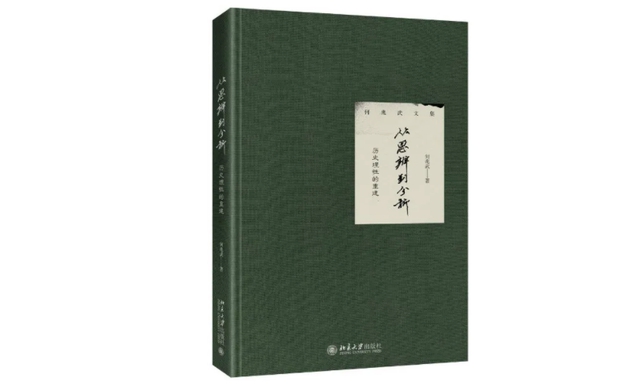
《从思辨到分析: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版
新京报:中国近代的史学传统注重实证研究、考据。但是何先生对思辨性的历史和思想史是有着深刻的兴趣的。在当时的氛围中,何先生对思想的兴趣,是由哪些原因促成的?
彭刚:每一个人的禀赋、兴趣不一样。比如我刚才谈到何先生的回忆,他年轻时候听各位史学大师的课,但是他更多感兴趣的是历史背后的理论问题。我想同样听这些人的课,别人可能更关注的是具体的问题,每个人有不同的兴趣倾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历史学当然要重视考证和史料。可是从古到今的大历史学家一定同时是一流的思想家,从司马迁到兰克,再到陈寅恪都是如此。今天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除了他的史料价值以外,他本身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决定了他对历史的探索和解释的力量。
比如说何先生在《上学记》中提到,听陈寅恪先生的课,除了史料和具体的论证以外,他更关心支撑陈先生学说背后的历史观和解释框架的精神力量,他感兴趣的是这些东西。包括何先生评价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也并不把他视作单纯的史料集成考证的集大成者,兰克学说背后自有着一套独特的历史观。何先生关心的是这样的问题。
他从来是一个害怕热闹、
喜欢清静的学者
新京报:许多读者了解何兆武都是通过《上学记》这本书,而读完这本书后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西南联大自由、宽松的学风。何先生这一批沐浴过联大自由学风的学者,他们有哪些魅力,使得我们如此神往?他们的哪些特质,是今天在科层化的学术体制中难以复制的?
彭刚:刚才有朋友告诉我,何兆武先生去世的消息变成了微博的热搜,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何先生从来是一个害怕热闹,喜欢清静的学者,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去世能够变得在学界之外也这么引人瞩目。
何先生的影响力在学界之外,或者说更普遍的对于公众的影响力,大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上学记》这本书,他对于他少年时代,尤其是青年时代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回忆,我想很多读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和何先生聊天,他就会谈聊到以前联大读书时候的事情,聊到当时在昆明的同学。他当时和我提到的同学,几乎没有我事先不知道的,他的很多同学都在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西南联大,我们不必神化,但是也确实值得我们缅怀、回望,值得我们高度的尊重。比如说为什么当时能够出这么多学术大师?一方面当时民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的人里面,最后能够成才的自然比率非常高。另一方面,比如说你看何先生的回忆录,我想很多西南联大前辈回忆中都是这样的,联大的学子们密切接触到的都是一批各个领域的、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学术开始成长并且达到相当高度那样一个时期的一批大学者。如果一个年轻的学子在他迈上学术道路之初,能够接触到这么多一流的大师,能够密切地接触,这对于他的眼界和成长太重要了。
很多人都强调西南联大的“自由”,我想,自由并不意味着放任,更不是懒散。西南联大的自由,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让学生有机会更从容地去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志趣。我们看何先生的经历,他一考进西南联大是读工学院,是要准备学建筑的,后来又转了学历史。他考研究生的时候先考的是外文,又转学哲学,后来兴趣又转移到历史,他不断地探索、发现、确认自己的志趣。我想何先生是这样,西南联大很多其他的前辈也都是这样的。

西南联大校门
新京报:无论是在五四时期,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与西学的交锋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何先生有着很好的古典文化修养,之后又对西学有着深刻的理解。何先生是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中学和西学之争的?
彭刚:何先生非常喜欢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时代和学术发展阶段不同,我们从不同的立足点出发研究中学、西学之间的关联,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
一方面,何先生在中学和西学方面都有非常深厚的修养。这在他的前辈里面并不罕见,可是在他的同辈里面就不那么多见,在后辈里面就更为少见了。所以,我想他是称得上中西皆通的,他的很多观点都有着足够的学养来支撑。
另一方面,何先生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看法,也特别清晰地带有深受五四熏陶的那一代人的印记。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表征的现代思想要素,构成了他的精神底色。所以他更多地强调中西思想和文化固然各有自己的特色,可是总有一些普遍的精神要素是超越地域的。比如何先生对于康德的热爱,这都与他的底色是分不开的。
换言之,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推动了现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些重要的要素,是何兆武先生这一代人非常在意、非常珍惜的。
新京报:何先生翻译了大量的康德的著作。康德对于启蒙的理解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何先生是怎么看待启蒙这个概念的?
彭刚:我想何先生关于启蒙具体的、直接的讨论并不多。但是你看他翻译的作品中——卢梭、康德、孔多塞等人的著作——都对启蒙有着很多直接的讨论。这也许就是他翻译很多东西的关怀所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方思想里面,对于构成了现代社会进步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是何先生特别重视,特别在意的。启蒙的遗产,是尊重个人的尊严、个人的自由,相信个体的理性、个体的努力,能够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复兴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我想这是何兆武先生终其一生的追求,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