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意识与问题意识
——读《北宋三大文人集团》
2022-04-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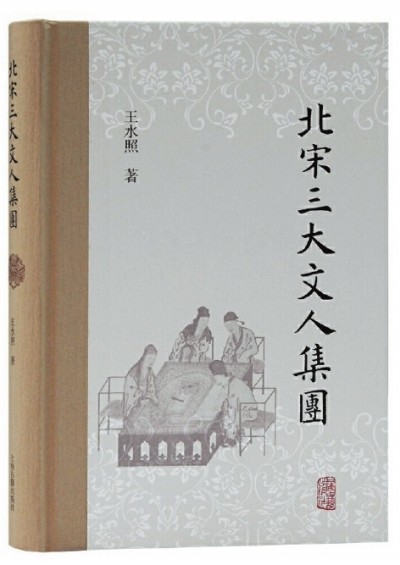
《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王水照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128.00元
202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水照先生的新作《北宋三大文人集团》,是他在四十年来发表的专题论文基础上整理、撰写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其中的一些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早已为学术界了解并接受,现在经过系统整理,集为一书,集中地呈现其长期研治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宋代文学史的最新成果,并显明地体现出其治学特色。
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不到三十万字。全书包括总论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的特征、文学结盟思想的文化背景的序论,分论钱(惟演)幕僚佐集团、欧(阳修)门进士集团、苏(轼)门“学士”集团的三章,和“结束语:后苏东坡时代”。王先生认为:“在北宋的文学群体中,以天圣时钱惟演的洛阳幕府僚佐集团、嘉祐时欧阳修汴京礼部举子集团、元祐时苏轼汴京‘学士’集团的发展层次最高,已带有某种文学社团的性质,对整个北宋文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序论》)
这部著作是王先生早就计划撰写的一部专著。1987年,他在复旦大学为助教进修班开设“北宋三大文人集团”课程时,这部著作的结构内容就已经了然于胸,可以行之于文了。他在当时的“教学大纲”上写道:“本课程力图在详细描述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的师承、交游、创作等情况的基础上,着重阐明文学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文人集团的成因、属性和特点,它们与北宋文学思潮、文学运动、诗词文创作发展的关系,群体又对各自成员的心态和创作所产生的交融、竞争等多种机制,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学的真实可感的历史内涵,从文学群体的特定视角对北宋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阐述和回答,探讨某些文学规律、经验和教训。”(《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后记》)王先生习惯于边研究、边授课、边写稿的工作方式,并不急于成书。经过近四十年的打磨,这部著作终于在我们弟子和出版社的催促中问世了,虽然王先生说还留下一些遗憾,还有计划中的章节未完成,但好在题目和要点在书中已露端倪,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体系完整、结构严密的成熟专著,反映了他对北宋文学的长期思考。值得一说的是,王先生虽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发表著述,有多种个人论文集、合著的多部专著传记、整理的多种古代典籍行世,早已著作等身,但这部著作却是他独撰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而且撰写的时间也是最久的,由此也可见王先生对这部著作和这个论题的重视。
一
读罢这部著作,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史家意识,或者说贯穿文学史的意识,是这部著作的一个显明特点。王先生指出,北宋这三大文人集团有一个互相连贯的特点,“以钱惟演、欧阳修、苏轼为领袖或盟主的文学群体,代代相沿,成一系列:前一集团都为后一集团培养了盟主,后一集团的领袖都是前一集团的骨干成员。因而在群体的文学观念、旨趣、风格、习尚等方面均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序论》)三大文人集团几乎囊括北宋全部的文学大家和名家,其中有欧阳修、梅尧臣、曾巩、王安石、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尤其是从欧门到苏门,标志着嘉祐、元祐时期两个文学高潮的到来。因此,王先生对北宋这三大文人集团的研究,就是叙写了一部简明精当的北宋文学史,但是又突破通常文学史教科书格局的写法,是以文学群体研究的专题出之。而这一突破是与王先生的治学经历分不开的。
王先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学起,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学习和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拥有老一辈的文学史家游国恩先生和青年中坚吴小如先生等名家。大学期间,王先生参加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集体署名的先后两部《中国文学史》的写作。1960年,他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文学研究所,他得到所长何其芳先生和前辈钱锺书先生等富有启发性的指导,又参加了文学研究所集体署名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1978年,王先生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至今一直从事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同事中治文学史的有老一辈的朱东润先生和与王先生同年的章培恒先生等名家。王先生在复旦教学相长,学术研究渐臻老成境界。在这部著作的新书研讨会上,王先生自述:“我参加过三部文学史的写作,我的学术经历如果用‘文学史’来贯穿,就是在北大学习文学史,从北大到社科院文研所是写作文学史,再到复旦是教学和研究文学史,但是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始终受制于文学史的教科书格局,即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作品个案研究为主干,这个模式对传授古代文学史的系统知识自然有其优点,但不能当作古代文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先生有意识地在这部著作中突破通常文学史的教科书格局,用文学群体作为考察对象。王先生认为:“文学群体是作家个人和社会(包括文学社会即文坛)联系的中介。文学作品在通常情况下乃是作家个人的精神劳动的产物,但他又不可能在完全封闭自足的心理结构中从事文学创作,必然受到社会环境、时代思潮、文坛风气等的深刻影响。作家个体自发的社会化要求,呼唤着文学群体的孕育诞生,而文学群体又促成个体的社会化得到发展和实现。个体从群体中获得大量的社会信息,感受到文学风会,培育和陶铸成自主独特的文学个性;群体则又以各个成员的代表者的资格,把群体的文学思想、观念、情趣、好尚、风格,影响于整个文坛和社会。群体在内部发挥着交融、竞争等多种机制,与外部又产生了各种纵贯、横摄的关联,由此构成一幅多方位、多层次的错综互动的文学图景。从文学群体入手来观察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不失为一条有效路径。”(《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结束语:后苏东坡时代》)
在这部著作中,王先生就是循着这一条路径从文学群体的角度来展开观察研究的,同时沿流讨源,串连起史的线索。例如,书中评述欧阳修从事古文写作的过程,历叙他向尹洙学古文到成为一代文宗,到与曾巩真脉相传。尹洙是钱(惟演)幕僚佐集团中专擅古文写作的重要作家,曾从北宋前期古文家穆修游。而欧阳修成为一代文宗的关键就在于其古文理论和写作实践都超越尹洙,奠定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群体风格,从而谱写出中国散文史上别放异彩的新篇章。这样的评述,就清晰地勾勒出北宋前中期古文的发展轨迹了。再如,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录取进士三百多名,其中有他的得意门生曾巩和后来成为欧门进士集团骨干的苏轼、苏辙等隽才。书中揭示了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认为这一事件对于欧门的组成、文风的改革乃至宋代文学的发展导向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北宋时期的第一个文学高潮也随之同时出现。
二
贯穿问题意识,是这部著作的又一个显明特点。王先生非常认可何其芳先生提出的为文要有三“新”(即新材料、新问题、新观点)的要求,力图在本书中借由视角的更换、单一个案分析模式的突破,发现一些新材料和新问题。由于是在论文基础上整理、撰写而成的,王先生的这部著作始终带着问题意识,在论述中抓住主要问题展开论述,随处可见他的独特之见,要言不烦。
例如,本书首次把钱慕僚佐集团引入文学史视野,将这一集团置于文学史的长廊之中,加以系统、全面的介绍。陈尚君先生在这部著作的新书研讨会上曾指出,朱东润先生在《梅尧臣传》中就对钱惟演治下的洛阳文人聚集这一现象略有所涉,但是王水照先生将这一问题充分地深化和展开了,对于诸如谢绛的作用、钱惟演文学上的宽容和奖掖后进、幕府人物的构成等等,都进行了完整、立体的勾勒与呈现。朱老认为,官为西京留守的钱惟演是洛阳的第一位大官,但是他是诗人,所以对作为诗人的梅尧臣等是平等看待的;梅尧臣的妻兄谢绛时任河南府通判,在洛阳的地位仅次于钱惟演,“在谢绛的领导下,洛阳成为诗人、文人的中心,文学史上所说的宋代诗文革新,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发动的”;“但是在当时并没有提出革新的要求”,梅尧臣、尹洙、欧阳修只是在钱惟演、谢绛两人领导下进行创作活动,“他们不但没有强烈的政治主张,甚至连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那样的创作动机也没有。这不是贬低梅尧臣等这一班人,而只是当时的事实”。作为一部传记,朱老的《梅尧臣传》是把钱惟演、谢绛等作为梅尧臣的交游来评述的,当然他也敏锐地指出了梅尧臣交游圈的特点。王先生则把这一交游圈提升到集团的高度,首次提出了钱幕僚佐集团这一现象。集团总有核心和盟主。即使这是一个没有打出旗号的集团。王先生指出,钱惟演“是一位充满政治权势欲望和艺术审美追求的矛盾复杂的人物”,他任西京留守时类似“文艺沙龙”主人的角色定位“直接促成了文人集团的形成”,其文学上的宽容和奖掖后进的精神的特点,使他在这一文人集团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是别人无法代替的。而欧阳修、梅尧臣等正是在他的宽容下取得创作的初步丰收。谢绛“不仅其官位仅次于钱惟演,而且在文人集团中的重要性也差可与钱氏比肩”,“以其文学才能和声誉成为这个集团的主盟人物”。王先生还对这一集团的构成人员做了详尽的考辨,对这一集团的特征做了精当的评析,认为“对文学和文化的共同爱好和热衷是这一文人群体聚合的基础”,“这是一个颇具互补互动功能、优化选择的文学群体,也便于取得文学整体上的优势和影响力”。这样,对这一文学集团的论述就很充分了。这是王先生对宋代文学尤其是北宋文学作了全面考察和长期研究后的发现。
再如,书中通过苏门《千秋岁》唱和词的研究,对词中所见元祐党人贬谪心态做了精微的分析,也具开创性。这些开创性的议题极大推动了北宋文学的深入研究。而对于学界多有研究或个人发现不多的论题,书中就不展开或从略。如鉴于欧阳修在文坛的主要贡献是领导古文运动,所以书中论欧(阳修)门进士集团这一章论述的聚焦点就落到散文方面,诗、词方面就从略了。这种抓住重要论题聚焦论述而非面面俱到的写法,也迥异于一般文学史的写法。
骆玉明先生曾评价王水照先生的学问有几个要点:“首先是王先生有‘一代之学’,即在宋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除了一代之学,王先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之学’,即整个中国古代的文章学”;“除了这两点外,还得说一说王先生的‘一以贯之之学’”,他所有的学术研究“一以贯之的是:努力地体会、理解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的传统,在文学研究的工作中对之加以继承和发扬,使之在当下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中起到有益的作用;而这一切,又并不背离现代的和世界性的视野”(见《半肖居问学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可以说,王先生的《北宋三大文人集团》这部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一代之学、一方面之学、一以贯之之学的成就。
“一以贯之之学”指的是王老师的治学方法。如果就王老师的治学领域来说,还可以补充和强调一下,王先生还有“一人之学”,即在苏轼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王先生是公认的当代苏轼研究第一人,他毕生治学的结晶《王水照文集》十卷本可望年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仅以苏轼研究为专题的就占了四卷。在《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第三章“苏(轼)门‘学士’”集团的各节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王先生研究苏轼及其苏门“学士”集团的广度和深度。
王先生的这部著作包括其先期发表的的相关论文已经在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其研究成果已经多为学界接受,其研究方法也足以为后学借鉴,堪称文学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作者:高克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