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智:铜山西崩,洛钟东响
——《牛津历史著作史》读后
2024-0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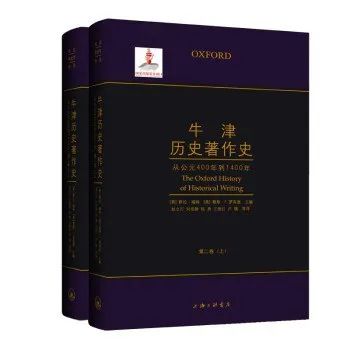
2011年,世界风云骤变,大事连连,这是世界政治年鉴编者之要务,且不赘言。在这里,我要说是年与我专业相关之一项要事:加拿大史学史家丹尼尔• 沃尔夫(Daniel Woolf,1958— )主编的单卷本《全球史学史》、五卷本《牛津历史著作史》相继出版,在我看来乃2011年世界史学史之伟业,在世界史学编年史上也留下了璀璨的华章。
新世纪伊始,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全球史学也应运迅猛发展,随之也迅速传入中国,较早见到的相关中文译本,是由伊格尔斯、王晴佳和穆赫吉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恰逢上述沃尔夫主编的两部史学史问世之时。这引起了中国学者陈恒的高度关注,随即谋划迻译,他先领衔主译了沃尔夫的《全球史学史》(陈恒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与此同时,又主编并与多位译者共同翻译了五卷本《牛津历史著作史》于2022年岁末一起推出。记得沃氏的《全球史学史》译就后,应陈恒之约,我以“建造巴别通天塔的伟业——序丹尼尔• 沃尔夫《全球史学史》”为题撰文。现今五卷沉甸甸的中译本《牛津历史著作史》,在我看来更是“建造巴别通天塔的伟业”,一项世界史学史编纂的伟业,其成就非凡,影响深远。
读皇皇巨著,需要时间和精力,方能观其旨,察其意也。为此,目前我只能略说一二。
其一,从西方史学史之史而言。
毋庸置疑,《牛津历史著作史》是西方史学史之史的一部新著,它继承传统,但又超越传统。西方史学史之史,或可溯源于古典时代古罗马卢奇安(Lucian,一译琉善,约120—180)的《论撰史》;萌芽于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史家波普利尼埃尔(La Popeliniere,1541—1608)1599年出版的《史学史》;奠定于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1824年的《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它被学界视为“史学的批判新时代的开端”;成熟于傅埃特(Eduard Fueter,1876—1928)的《近代史学史》(1911)、古奇(G. P. Gooch,1873—1965)的《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13)。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学界的历史著作史的写作,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先后问世的有:巴恩斯(H. E. Barnes,1889—1968)的《历史著作史》(1937)、绍特威尔(J. T. Shotwell,1874—1965)的《史学史》(1939)和汤普森(J. W. Thompson,1869—1941)的《历史著作史》(1942)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甚,为我国学界所熟知的中译著作有: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唐纳德• 凯利(Donald R. Kelley,1931— )的《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恩斯特• 布赖萨赫(Ernst Breisach)的《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等。
丹尼尔• 沃尔夫主编的《牛津历史著作史》确是在继承西方史学史书写传统的基础上,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地开拓创新,为史学史的编纂彰显了别开生面的新景象。略举一例证之:1942年汤普森的二卷本《历史著作史》问世,70年后,即2011年沃尔夫主编的五卷本《牛津历史著作史》付梓,两者书名同一(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就总体来看,其文脉与旨意也是相通的。然而,70年来,时代的变革与社会的进步,推动了历史学的不断发展,从西方新史学的演变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兴起,从全球史的编纂到全球史学的蔓延,《牛津历史著作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沃尔夫主编和全书撰稿者力图在全球视野下,合力书写涵盖从古代世界到现当代世界各国各民族史学的历史著作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部宏伟的世界史学史,与上述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之类的西方史学史相较,两者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二,从史学史学科本身而言。
以纵横论之,《牛津历史著作史》不仅就纵向即西方史学史之史的进展而言是出类拔萃的,而且从横向与同时代的著作(比如伊格尔斯等合著的《全球史学史》)相比也是佼佼者。陈恒教授指出:“《牛津历史著作史》是一套由众多学者合作编撰、涵盖全球的史学史著作,全书由150篇专论组成,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涵括整个人类史学文化传统的历史著作史。”确实,这套宽厚的学术著作为我们研究世界史学史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案头书,正是:全球眼光,瀛寰回眸;彰往察来,无问西东。无疑,众人修史,也有难以避免的缺憾,正如安德鲁• 菲尔德、格兰特• 哈代在本书第一卷《导论》中所言:“这套丛书是由超过150位现代学者编纂而成。每位学者承担着历史著述某些方面的任务,但是都置于一个清晰的时间和地理框架内。虽然这种表现不一的设计类型可能会显得混乱,但是整套可能会是一部更为可靠,且内容奇妙缤纷的作品,其中蕴含的创造力正是赋予人类趋向回溯过去、探究历史意义的特征。”群贤奋力写史,终成硕果。
从史学史学科来看,《牛津历史著作史》突出的或创造性的亮点在哪里?我个人肤浅地观之有三:一是全球性。记得在我国坊间流传的《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书一开篇就说:“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站在月球上观察地球,对人类历史进行全球的考察,确是现当代历史学编纂的一个亮点,《牛津历史著作史》尤甚。二是客观性。斯塔夫里阿诺斯上述之语,也语涵客观性:站在月球上考察全球,就可看出伦敦或巴黎、北京或新德里观点之差异,对此就有作出客观评价的可能性。可以看得出来,本书撰稿者们力意在各篇章中疏离“欧洲中心论”,打破陈规。三是创造性。本书创新的亮点甚多,比如突破传统的“四分法”,设计了一个崭新的从开端至当今的世界史学史之分期,沃尔夫们大胆创新,成就了一个新的分期,也成就了本书的一个最大亮点。各卷各有千秋,各篇各有特色。对此,读后便会发觉并非虚言。
其三,从中外史学交流史而言。
我国有丰富的史学遗产,但在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过程中,需要寻找一条沟通中外史学交流的路径。为此,中外史学交流就显得格外重要。倘在“司马迁从未听说过修昔底德,塔西佗也完全不认识同时代的班固”(见本书第一卷“导论”语)的时代,缺乏史学文化之间的互通,人类文明总会显得苍白而缺乏厚重与张力。须知,史学交流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舍之史学会日渐枯亡。进言之,一部全球的历史著作史,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书写的,不同国家和民族史学之间交流互鉴,比较异同,方能使世界史学变得丰赡且各具特色,散发出各自独特的个性和持久的生命力,正如杜维运所言:“将各国史学放在一起作比较,由比较可以知其异同,由异同可以求得会通、综合之道,到求得会通、综合之道时,就是一种创新了。”
当下,《牛津历史著作史》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外交流史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取之宏富的教科书。深读五大卷150篇的华章,会有一种感觉,犹如深山寻宝,不时会有新发现。略举一例:第三卷第三十章由凯瑟琳• 朱利安执笔的《印加历史的形式》,该文搜集罕见的史料,从印加的历史形式(绳结、花瓶、纺织品等)出发,进而考察了欧洲与印加历史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外来传统对印加历史书写的影响,这不正是域外两地(欧洲与中美洲)之间史学交流的一个典型案例吗?这种难得的史学交流案例,还散落在各卷中,等待寻宝者来深挖之。由此,这也是我们要进一步拓宽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总要前行。“铜山西崩,洛钟东响”是出自我国典故的成语,其原意实为山崩地震而产生的共振共鸣,后据传说记之,比喻重大事件的相互感应和相互影响。因此,五卷本《牛津历史著作史》的问世及其后中译本的出版,为21世纪域外史学东传留下了中国学者深重的足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倘要观大变局之头绪,察大变局之足迹,历史研究是大有作为的,历史书写的古今演变也正是前者的题中之义。为此,我们既需要有勇攀高峰的魄力,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毅力,在与国际史学发展的互动中前行,不断贡献出能体现中国历史著作特色的学术精品,为书写世界史学史的伟业做出中国历史学家的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