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高昊:鸦片战争的起源与英帝国视野中的中国
2022-06-02
【编者按】从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开始,西方人逐步走了出过去几个世纪对中国的一些凭空想象。特别是,英国通过使团活动和大规模的贸易往来,获得了更多与清朝政府及人民近距离交往的机会。在两国的这些直接相会中产生的种种中国形象,深刻地影响着英帝国的对华政策。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半个世纪里,不同群体塑造了哪些中国形象?他们又怎样依此为英国的对华政策献计献策?英政府最终决定对中国发动远征与这些形象和认识又有何关联?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副教授高昊的近著Creating the Opium War: British Imperial Attitudes towards China,1792─1840,正是从这些角度来关注鸦片战争爆发的观念背景。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之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邹子澄在英国访学期间专访了作者高昊,请他谈谈这部书背后的研究经历以及书中的主要观点。

高昊,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帝国与全球史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与考古学院国际事务主任,爱丁堡大学博士。学术成果发表于History, Histor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Britain and the World等国际著名学术刊物,著有专著Creating the Opium War: British Imperial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1792─1840。现任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UKCHA)英方领导院校学术主任、英方学术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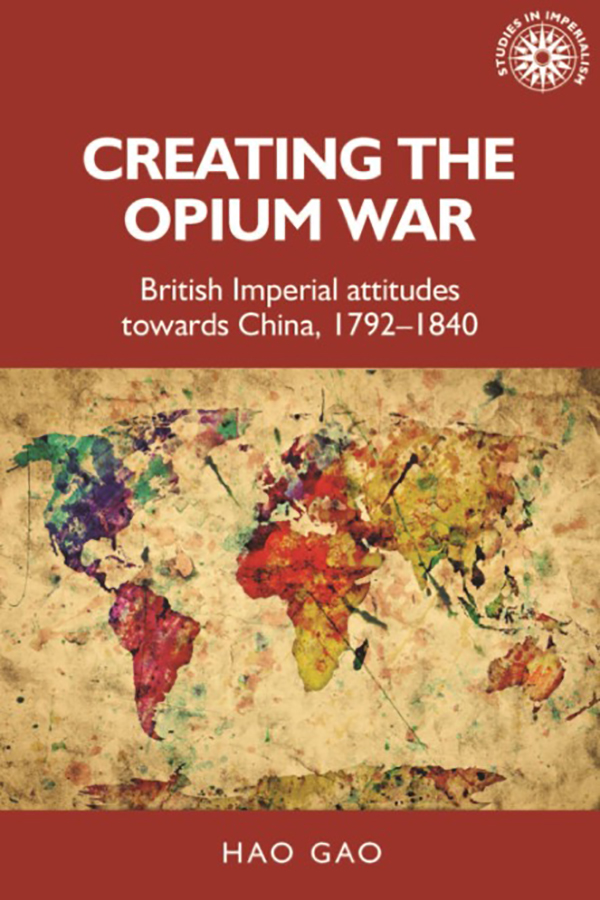
澎湃新闻:首先能否请您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
高昊:我是2009年赴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来英国前师从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读博期间的导师是哈里•迪金森(Harry Dickinson)教授。两位老师在各自国家的史学界均是代表性人物,他们的治学思路都深深影响了我。如果要细谈两位先生的学术观点和对我的具体帮助,可能各写一本书都不够,所以还烦请感兴趣的朋友们自行了解他们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澎湃新闻:您最初是怎样将研究目光放在英中两国的交往上的?
高昊:刚来英国时,带着国内研究生的某种心态,想做一个所谓“纯英国史”的题目,但一开始迪金森教授便提醒我这样的想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很难分清什么是“纯英国史”,什么是非英国史(non─British history)。不光英国如此,应该说,几乎任何历史事件都一定要放到全球的背景中去审视、去考察。
过去的这十几年中,英国大学教育一个显著的转向,就是人们开始认识到“British history”这样一个看似再正常不过的叫法,实际上是有潜在问题的——因为以一种割裂的、排他的眼光来看待英国(或者任何一国)的历史,不仅会忽视世界不同地区间千丝万缕的关联,甚至还有孕育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
随着这一观念的推进,当前在英国只有少数大学还存在以“英国史”为标题的历史课程,绝大多数学校的历史系已选用更精准、更宏观或更微观的课程名来教授与英国历史相关的内容了。总之,我很高兴迪金森教授在一开始就帮我指出“纯英国史”这一提法的弊病,在学术方法和观念上我才不用走一条弯路。
在决定把眼光转向英国与世界的交流后,英中两大帝国的互动自然成为我的一个重要备选项。当我在迟疑要不要避开中国时,另外一位教授的话打动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你会认为研究英国与牙买加、南非或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会比研究中英两国更高级、更有趣、更有学术价值吗?”我至今仍时常想起这句话,如果谁真会去这么想,那还谈什么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呢?从这之后,我就确定要把中英两国的交往、互动与碰撞作为我的主要研究对象了。
澎湃新闻:在确定大方向后,您又怎样进一步关注到鸦片战争,尤其是鸦片战争的“前史”呢?
高昊:这个项目刚开始时,我们的想法是做一部关于英国人怎么“想”的历史。当然,根据不同的学术路数,这样一个课题有不同的做法。传统一点看,这可以是一部思想史、文化史,按新一些的说法,可以叫它中国观或中国形象研究,更新一点的提法就是心态史、观念史、甚至是情感史了。
由于迪金森教授的专长是“漫长的十八世纪(1688─1832)”,我们的落眼点自然放在了鸦片战争之前。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个人感觉不太满足于只简简单单地研究英国人怎么去“想”中国。一来,我认为要是能把英国人怎么去“想”和他们在中国怎么去“做”联系起来,这样研究能更有深度。这使我将研究重点聚焦在中英间的直接相会(direct encounters)上,而不是英国人在本土的小酒馆或是大庄园里怎样凭空想象那个远方的中国。
二来,无论人们怎样去想,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这又和一整套话语、形象密不可分。这样的话语和形象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存在又怎样反过来左右人们怎样去想、去理解中国,进而为英国的对华政策献计献策?如果能把这种相互影响搞清楚,那么这样一个研究就有可能再上一个台阶,去解释前人没能触及的一些重要学术问题。
澎湃新闻:为什么选择1793─1840这样一个时间段?
高昊:首先,1793年发生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和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长期以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此前几乎没有任何研究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考察。这期间的半个世纪时间,相比鸦片战争之后的大量学术研究,受到的关注要少很多,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学术空白。
第二,我记得我在本科生的时候,曾作为外国学者的翻译参加过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上,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先生借用年鉴学派的提法,指出当时学术研究中有太多“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研究和“短时段(courte durée)”的研究,而扎扎实实的“中时段(moyenne durée)”研究相当缺乏。而1793─1840这几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段,正好是一个不长不短的“中时段”。
澎湃新闻:这个“中时段”和鸦片战争的起源有什么关系?
高昊:我的博士导师迪金森教授时常教导学生们说,研究选题好比照相。同样一个场景,选择用不同的焦段摄影,往往能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画面。比方说,一幅风景画,用广角拍,可能是蓝天白云、绿草如茵,用中焦拍,可能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在草地上嬉戏打闹,而用长焦的话,或许拍到的是枝头正在筑巢的那几只小鸟。换句话说,在做历史研究时,即便别人也在某处照过相,通过变换焦段、选择对象,学者们完全可以呈现出各有特色的学术“照片”。
基于上述几点考虑,加之我个人的摸索与思考,我发现探究英国人在这半个世纪里逐渐变化的中国观念、对华心态,可以对鸦片战争的起源这一重大学术问题上进行关键的补充。
所以,我一方面按照传统史学的思路,考察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的决策者(如英国首相、外相、访华使团领导层等),另一方面从帝国史和全球史的视角,关注那些缺少直接权力、却亲身参与过英中交往的各级人士(包括常年在华的商人、传教士和访华使团的中下层等)。这样,把相关的政府档案、议会记录、官方通信和英人访华的日记、回忆录、新闻评论等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更立体的图景。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相互作用,逐渐塑造出当时英方对于中国的主流认识,乃至衍生出某些关键话语,影响英帝国的对华政策。这种转变的中国观,或者说对华心态,是鸦片战争起源的重要背景。
澎湃新闻: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对华心态决定了鸦片战争的爆发吗?
高昊:这当然不是我的意思。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的研究目标不是要去推翻前人关于战争爆发的种种观点,也不是要(按照英国人的话说)把自己的手指头放在某个特定的因素上,然后说“看,就是它引发了鸦片战争”。我真正想做的,是要通过一个扎扎实实的中时段研究,为战争的起源整理出一条潜在的新线索。这条线索不是去断言什么样的中国形象就一定会引发战争,而是要让人们看清楚如若没有这些庞杂的、既有延续又有变化的对华观念、认识和想象,中英间的这场战事就不会爆发。
因此,我的研究不是去宏观地探讨哪些经济、政治或是文化因素直接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不是去挑战这些既有的观点,而是去考察这场冲突出现的观念背景和所谓“语境”——即英国人在鸦片战争前的半个世纪里,是怎样逐渐认为一场对华战争是合理、可行、乃至一定能取胜的。这是以往人们在讨论鸦片战争起源时所忽视的面向。
如果借用数学的语言说,我关注的不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充分条件,而是它的必要条件。
澎湃新闻:您专著的第一部分有两章,分别探讨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和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的在华活动。对于前者,因为它是历史上英国官方的首次访华,学界似乎已有不少研究。学者们的着眼点通常在觐见礼仪和通商诉求等问题,最近又有人从翻译和历史书写等角度重新理解其意义和影响。您在书中是怎样关注马戛尔尼使团的?
高昊:有关马戛尔尼的研究虽有不少,但说起来其实总很难离开何伟亚的《怀柔远人》,以及围绕它的种种争论。因此,大家对该使团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某些既有的研究框架。
我在书中尝试跳出这些传统框架来看待这次使团。特别是,我更多地把目光投向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这两人以外,来了解使团的中下层人士的中国印象和对使团事务的想法。这些人包括马戛尔尼的侍从爱尼斯•安德森(Aeneas Anderson)和负责展示天象仪的科学家、机械师詹姆斯•丁威迪(James Dinwiddie)等。他们都留下了访华的日记,回英后出版成册,但这些记载在过去的研究中常被忽视。我在书中尝试把他们的见解和使团领导层的观点对照起来,这样能对使团的在华经历形成一些新的认识。
澎湃新闻:关于这些新认识,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
高昊:比方说,我发现,使团内部对于英方的某些决策乃至对使团的总体评价,是存在不同意见的。马戛尔尼和斯当东作为领导人、决策人,力图捕捉和渲染使团活动中积极成功的一面。为此,他们会去有意无意地掩盖那些与这一印象相左的事实,这造成他们的叙述有时与其他使团成员的回忆相矛盾。
其中一个例子表现在使团的所谓“科技展示”上。关于这个问题,传统说法是清朝官员傲慢自大,看不起英国人不远万里带来展示的各种器物,就连在当时英人看来科技含量很高的天象仪,中方看见也不屑一顾。这一印象其实是延续了当时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的说法,因为他们要表现中国人的闭目塞听、自以为是,而不是自己的决策有什么问题。
作为器物展示的总负责人,丁威迪其实对此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天象仪没有达到想象中的震撼效果,是因为英方领导人制定的相关展示策略不够恰当、不够细致。丁威迪指出,他在圆明园拿出天象仪时,是一堆堆拆散的零件。由于仪器精密复杂,他和助手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组装完毕,而这整个过程被中方目睹,包括组装时不可避免的很多调试和操作失误。他认为,英方未能保证这些仪器在组装好之后一起拿出来展示,是没有震撼到中国人的重要原因,而马噶尔尼和斯当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使团中下层成员像这样批评领导层决策的例子,我在书里还谈了不少。总之,马戛尔尼和斯当东作为使团领导人,从未承认他们的使团是失败的,反倒是喜欢突出在他们自己看来成功的一面,这与我们传统上对该使团的认识是有一定出入的。
另外,我在书中还澄清了一个关于此次使团的误解。之前有不少观点认为从马戛尔尼开始,英国就有武力攻华的打算了,因为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谈到英方只需用几艘小型护卫舰(frigates)就可以摧毁整个中国的海防。据此,甚至有人就此下结论认为从这时候开始,一场中国和英国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然而,如果仔细阅读马戛尔尼的日记,我们就会看到这是一种断章取义。紧接着上面那句话,马戛尔尼实际上明确表示这并不是他所想要看到的结果。他说,中英间如若开战的话,英国一定可以轻松取胜,但是,此为英国的下下策,因为战争会给英国的经济特别是其东方帝国造成巨大伤害,因此,只要有一线和平的希望,英方都不应该懂使用武力的念头。
此类误解之所以产生,大概是源于过去的某些研究试图简单地在马戛尔尼使团和鸦片战争之间寻找某些联系,却忽略了期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英双方的种种其他互动,比方说1816年的第二次使团,因此,才会产生这种经不起推敲的说法。
澎湃新闻:关于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之前的研究似乎就很少了。
高昊:的确是这样的。我在2014年曾在英国的History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从英国对华认识的角度,来定义该使团的历史地位。这可能是关于阿美士徳使团的第一篇有影响力的专题学术论文,因为此前不管在英文还是中文学界,对这个使团几乎都没有什么深入研究。最近这几年,英文学界涌现出一批关于阿美士徳使团的论文甚至论著,这其中有不少都是从我这篇文章的视角下延伸出来的。某种程度上说,阿美士徳使团已成为当前领域内一个不大不小的研究热点。
澎湃新闻:为什么之前人们对阿美士德使团缺乏关注?而您的研究对它又展现了哪些新的认识呢?
高昊:这个使团以往被忽略,主要是因为没有英使阿美士徳未能得以觐见嘉庆帝。和1793年马戛尔尼几次或远或近地亲眼见到乾隆帝相比,1816年的这次使团自然看起来没那么引人注目了。然而,通过研究,我却发现这次看似不起眼的中英接触实际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相比马戛尔尼使团留下的历史文献,关于阿美士徳使团的一手史料更加充分。尽管阿美士德本人的手稿因为回程时的一次沉船事件遗失了,但很多其他使团成员留下的记录仍保留至今。我在做这部分研究的时候,就利用了11位成员写下的超过15种文献。
再者,阿美士徳使团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其是否和皇帝见上了面,而在于这次使团为英人实地考察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使团从京师返回广州的旅程长达四个多月。相对于马戛尔尼使团,1816年英人的这次“在华旅行”不仅受限更少,能够更自由地探索沿途城镇乡村,和当地居民直接接触,而且还途经了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清王朝一直引以为傲的“大好河山”。这样的机会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
然而,此时已是清代盛世以后的衰落期,使团一路所见的萧条景象,印证了很多他们之前有所耳闻、却又不敢确信的负面中国形象。加之此时的英国本土正经历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巨大的反差让使团成员们对当时的中国国力情况产生了更清醒、更直观的认识。
另外,由于沿途大多数中国民众对英人都表现出友好的态度,这使得使团中的不少人认定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普罗大众,而在于那个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满清政府,特别是嘉庆帝本人。他们认为正是这一小撮人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开放。
基于阿美士徳使团产生的这一系列新的对华认识,英人在此后提到对华强硬时,心里便更有底气了。哪怕是对华动武的念头,不但提起来更容易让人接受,而且对中方抵抗能力的顾虑也少了很多。当然,我们不能说在这个时候中英间的战事就已不可避免了,但无论如何,相比之前,针对清王朝的军事行动在英国人的脑海里已经是一件更能想象(more imaginable)的事情了。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还提到阿美士德使团内部的一场“礼仪之争”,这个以前好像也没有被提到过。
高昊:应该是这样的。这里我主要关注的是使团内部关于是否要向嘉庆帝叩头的争论。我借用James Polachek那本The Inner Opium War的书名,把它称作“Inner Kowtow Controversy”——因为以前人们总认为向不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是中方和英方之间的争议,而没有看到对此问题实际上英方内部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尤其是在阿美士徳使团时。
1816年这次争议的核心人物,是当时自认为最了解中国的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93年时,马噶尔尼使团中几乎没有人了解中国,而在阿美使团里,有五到六人算得上是懂些中文,除身为使团副使、后来成为汉学家的小斯当东外,还包括已有数年在华经历的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等。因为这些人掌握着所谓的“本地知识(local inside knowledge)”,故而阿美士德不得不经常请教他们的看法。
在谈到叩头问题时,一开始,阿美士德本人和使团三号人物亨利•艾利斯(Henry Ellis)其实并不排斥屈从中国礼仪,即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但小斯当东对此强势反对,他坚称基于自己对中国的了解,若阿美士徳在此问题上屈服于清廷,对英方有百害而无一利。
为影响最后的决策,小斯当东还抖了个“机灵”。他声称鉴于此事关重大,到底叩不叩头不能由他们领导层的三个人草率决定,而是要将所有具有“本地知识”的人士(即其他五人)都拉进来,做集体决定。这样,小斯当东就巧妙地转1:2的劣势为6:2的胜势,最后成功说服阿美士徳拒绝遵从中方礼仪。而这一强硬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觐见被嘉庆帝断然拒绝。
和前一次相似,阿美士德使团主要领导成员在事后也都避谈这次使团内部的叩头之争。由于决定毕竟是集体做出的,在谈及使团觐见失败的原因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把责任放在了嘉庆帝身上,认为其不够大度、反复无常,远不及其父乾隆帝,这样又进一步为当时中国社会的萧条和落后找到了(他们所认为的)根源。
澎湃新闻:您书的第二部分由三章组成,集中讨论两次使团之后,英方中国观的变化和对华政策的形成。这一部分篇幅很大,能否简单谈一谈这里面您感觉很重要的一两个点?
高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是1833年前后。以前我们在研究鸦片战争时,通常将目光聚焦在1839、1840上,而对此前中英贸易的一些重要变化谈得不多。1833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这一年开始,英方正式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在华贸易特权。
在此之前,在华英人群体是可以大体分为两派的。一派是东印度公司的驻华商人,他们和中方的关系虽然起起伏伏,但总体上算是说得过去。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是组织种植鸦片的,但在中国他们只从事以茶叶为主的合法贸易。另一派是直接在华从事鸦片走私的所谓“自由商人”(或“散商”),这些人虽然也来自英国(当然,还有其他国家),但不管是东印度公司还是广东政府,对他们的行为难以形成真正的约束,加之背后的很多利益关联,长久以来也没有人去真正阻止他们的走私行为。
从我的研究视角看,最关键的是,这两派英国人对于中国是怎样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文明,以及英国对华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是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的。这意味着在1833年之前,英方实际存在着两套截然不同的对华观念:
东印度公司一方认为中国有着相对发达的文明,主张尊重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要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和中国人做生意,倾向于对华温和。特别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个讲道理的民族,要和他们慢慢说理,引导中国慢慢开放市场,不可操之过急,特别是要以东印度公司为核心,开展对华贸易。
而“自由商人”一方则倾向于挑战这种温和的对华政策,他们针锋相对地构建了另一套中国形象。在他们口中,清王朝下的中国文明是落后的、法制是腐朽的,而中国人民迫切渴望外部知识,希望拓展国际交往和贸易,因此,挑战清政府的法律和权威并不缺少合法性。针对中国人讲理的形象,他们还特别提出,清朝朝廷是特别吃硬不吃软的,只有对华强硬,才能为英中双方共同打开两国贸易的新局面。
客观来看,这两派英国人提出各自的中国认识,都有着背后的经济目的,而这场商人间的对话,毕竟不是一场学术上的争论——在当时并没有人去仔细推敲究竟谁的话更有道理、谁呈现的中国形象更符合事实。在自由贸易的风潮之下,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垄断集团和他们的种种言论在当时是被广为诟病的。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营权取消,基本宣告东印度公司退出历史舞台。随着“自由商人”们取得事实上的胜利,他们所呈现的那套中国观,特别是对华应采取强硬态度的主张,也逐渐被更多人接受,甚至开始成为当时的“主流话语”。
澎湃新闻:这个关于中国形象的争论的确在以往被大家忽略了。另外,我从您的书中了解到,关于1840年英国议会发动鸦片战争的那次投票,我们在过去也存在一些误传,对待史实的理解有疏漏之处,您能不能具体谈谈?
高昊:是的,准确来说,战争不是英国议会发动的,而是英国政府。战争决定也不是1840年做出的,而是1839年。
关于那次议会投票,一般流传的说法是,1840年4月7日,经过英国议会下院的辩论,英方以271票支持、262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对华动武的决定。然而,如果仔细推敲史实,就能发现当中疑点重重。首先,如果英方1840年4月才做出战争决定,当年6月份的时候英军就已兵临广东水域了。根据当时的通讯速度,这个完全说不通。再者,从当时议会记录的原文中,我们可以看到,262票投给的是YES,271票投给的是NO,而不是颠倒过来,这说明当时的投票议题和大家之前理解的也有出入。
澎湃新闻: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高昊:英方真正决定对华出兵的时间是1839年10月1日。当天,在温莎城堡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辉格党政府秘密通过了对华派遣远征军的决议。这个时间点和后来战争开打的时间才是吻合的。
政府决定对华动武的这个消息是在此后的几个月中渐渐流传开来,特别是被反对党托利党知晓的。1840年4月7日的那次议会讨论,严格意义上说,是托利党发起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motion of no confidence,俗称“倒阁”),目的是推当届政府下台。而辩论及投票的真正主题,不是英国是否应当对华动武,而是辉格党政府是否在中国事务上表现失职,“疏于预见和预防(want of foresight and precaution)”。这就解释了前面提到的YES和NO颠倒的问题——而最终的结果是,辉格党以微弱优势得以继续执政,托利党此次“倒阁”失败。
澎湃新闻:辉格党政府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向中国开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和规定呢?
高昊:这个问题不光是中国学者,很多西方学者也搞不清楚,只有对当时英国的政党政治规则有足够了解,才能有清楚的答案。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当时英国的政治制度下,这其实没有任何问题。拥有行政权的政府(the executive)不需要得到议会的同意即可开战或媾和。
然而,虽然政府有权发起战争,但战争通常都需要高昂的税收作为财政上的保障,而议会作为立法者(the legislature)有权通过法律和就征税问题投票,所以,任何战争想要顺利地打下去,都离不开议会的支持。
换句话说,虽然议会无权干预政府对任何国家宣战,但在此之后,议会有能力左右政府是否继续这一战争。这样一来,我们就解释了为什么这场关于中国问题的议会辩论发生在辉格党政府做出战争决定之后,而不是之前了,但不管怎么说,无论那次投票的结果如何,都不能改变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大批开到中国沿海的事实。
当然,后面的故事是在7月27日,议会下院再次开会,决议向远征军拨款作为战争费用。1841年6月,托利党又一次发起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这次他们以一票的优势险胜。辉格党不得不选择解散政府,举行大选。托利党在这次选举中获胜,于1841年8月底如愿以偿地成为执政党。这时,鸦片战争已开始一年多的时间,以罗伯特•皮尔(Sir Robert Peel, 2nd Baronet)为首相的新政府没有选择中止战争,英国远征军继续对华作战,直至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澎湃新闻:我读您这本书,觉得它的一大特色是很难用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路数来简单地概括它。它肯定不是循规蹈矩的传统史学,但也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传统史学中很多扎实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它是帝国史、全球史,但同时又没有离开民族国家。
高昊:谢谢你的精彩点评!是这样的,其实这也代表了近些年学术研究的一个新动向。最早的时候,人们研究传统史学、特别是政治史时,讲究自上而下(top─down)。几十年前,以所谓“新文化史”为代表的一批“新史学”开始关注自下而上(bottom─up)。而现在,“新文化史”早已经不“新”了,实际上,最近十几年在英国学界几乎很少有人还用这样的提法。目前最新的路径是关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把它们贯通起来。正像我在这本书中所做的一样,通过自下而上的一些材料和观点,来结合自上而下的问题和框架,通过帝国史、全球史的视角,来回答传统外交史、国际关系史中的重大问题,从而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关于民族国家史学和全球史,我想说的是,历史学家们实际上从来都不应该是竞争的关系,而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也很难给所有学者和著作加上一个“民族国家”或是“全球史”的帽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学术观点、路径都可能是丰富的、而非单一的。同样一个人,可能有时受民族国家史学的影响多一点,有时受全球史的影响多一点。同样一本书,可能这里是传统史学,那里是全球史,我们不应该把它们不经区分地割裂开来。
其实民族国家也好,全球史也好,只要我们都抛弃一个非此即彼、此优彼劣的滤镜,大家就能以一个更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有时甚至谈不上“彼此”,因为很多时候“此”中有“彼”,“彼”中有“此”。还是那句话,历史学者是合作者,不是竞争者。
澎湃新闻:您选择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的“帝国主义研究丛书(Studies in Imperialism)”是不是就是出于相关的考虑?
高昊:是这样的。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帝国主义研究”系列丛书是西方史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品牌,在帝国史领域可以算是首屈一指了。当时对方发出邀约,表明希望把我这本书放在“帝国主义研究”丛书中,我便欣然把书稿交给他们——因为这可以保证这本书的读者不单单是某一两个领域的学者或学生,很多对帝国史、全球史或其他领域感兴趣的读者都可能注意到它。我们现在研究的方向本身就是越来越跨领域、跨学科、跨国别(或者说去国别的),各种条条框框,当然越少越好。
澎湃新闻:这本书的定价是八十英镑,与国内图书相比是比较高的价格了。
高昊:哈,英美学界一般刚出一本新书,基本都是这个价格。出版社都是先出精装版和电子版,主要面向世界各大院校、图书馆等。等这些财力雄厚的机构买得差不多了,一两年后再出平装版,供普通消费者购买。平装版的价格要低廉得多,只要二十多英镑,在各大书店和网上都有销售。我的这本书是2020年出的精装版,现在平装版刚出,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关注。
澎湃新闻:就目前的读者反馈来看,英美这两国的学者对于这部作品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或视角吗?
高昊:我不太赞成做“英美学者”这样的区分。每个人的学术背景、个人经历都不同,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受教过的人也不同,很难简单地用他们来自什么国家来评价他们的学问。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用国别把一拨人和另一拨人区分开来,来关注他们的差异,那么这样的区别可能就会越看越多。但如果我们不先去做这样的主观认定,往往就能从彼此的身上发现更多的共同点。文化互视常常都是这样,“同”还是“异”很多时候取决于你自己倾向于往哪方面看。
我相信,对于世界各地的历史学者们来说,大家不管生活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是干着大致相同的事情——行走于一二手史料之间,尝试提出自己新的见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不倾向于在“学者”二字前面加上一个什么国别。当然,仅从地理意义上说肯定是可以的,某个学者来自英国就是英国,美国就是美国,但从学术上讲每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者,有什么样的学问,不应当由他们来自某某国家所定义。
更直接一点回答你的问题,我没有发现英美两国的学者对我的作品有什么特别不同的观点或视角。如果读者有什么不一样的评价,我相信也不是由他们来自什么国家来区分的。
澎湃新闻:您目前有没有出中文翻译版的打算?
高昊:之前也有朋友提过这个想法,但我目前没有出中文翻译版的打算。我一直相信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因为任何两种语言做到百分百的互译都是不可能的。就拿我这本书的书名Creating the Opium War来说,在英文里这是一个非常通顺、甚至是挺出彩的题目,不少同事都赞赏说我书的名字起得好,但“create”这样一个词就很难精准地翻译成中文。
在中文里,“create”一般译成“创造”或是“制造”,但在中文母语者的脑海里,“创造”通常是和“发明”连在一起的,“制造”是和“生产”密切相关的,这些都与我在英文中想用“create”表达的原意相去甚远。若译成“建构”或“构建”,听起来可能学术一些,但实际上也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甚至会引起误解——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场鸦片战争是“建构”起来的。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的关注点是这场战争是如何在英国人心中变得越来越能够想象、能够接受的,但这不是什么“建构”。
所以,恳请大家不要把我这本书的书名译为《制造鸦片战争》或是《建构鸦片战争》什么的。你想想,这才是一本书的第一个词,如果把整本书都翻译过来,与原文的差距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对于读者们来说,读任何学术书籍,看原文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只有原文才能带来与作者的直接对话感。换句话说,任何非作者本人的翻译都是一种间接的解读。一些西方学者要想把作品变成中文,依赖翻译是不得已的事情,而中文是我的母语,所以暂时不出中文版也是出于对读者负责的考虑。
另外,我不是那种自己出一本书,就希望所有人都要来读的学者,恨不得机场电视、田间地头都能看见它的身影。同时,我又非常期待所有真心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读者,能够认真地通过我本人的文字来了解这个研究。我相信对于这部分读者来说,若真有意愿来读,语言能力不会是太大的问题,而语言能力本身,也是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逐渐提高的。我自己在当学生时,也是这样的读书态度。
当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我肯定会考虑在原书的基础上再加工、再创作,做一本原汁原味的中文版,和更多的中文读者直接对话,但目前还是烦请大家找英文版来看,那里面的字字句句,才是我真心想要表达的意思。
(澎湃新闻特约记者:邹子澄;采访:高昊/审校;责任编辑:彭珊珊;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