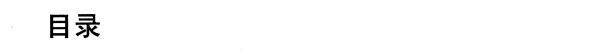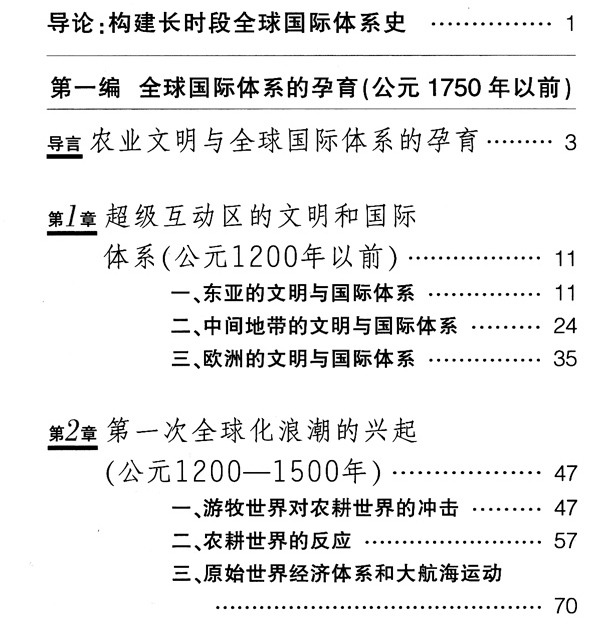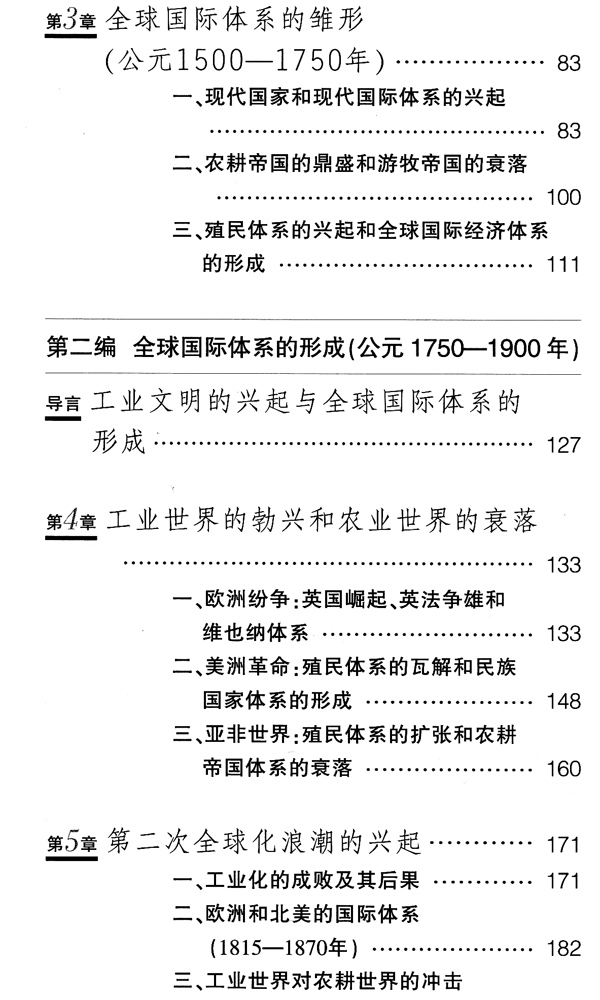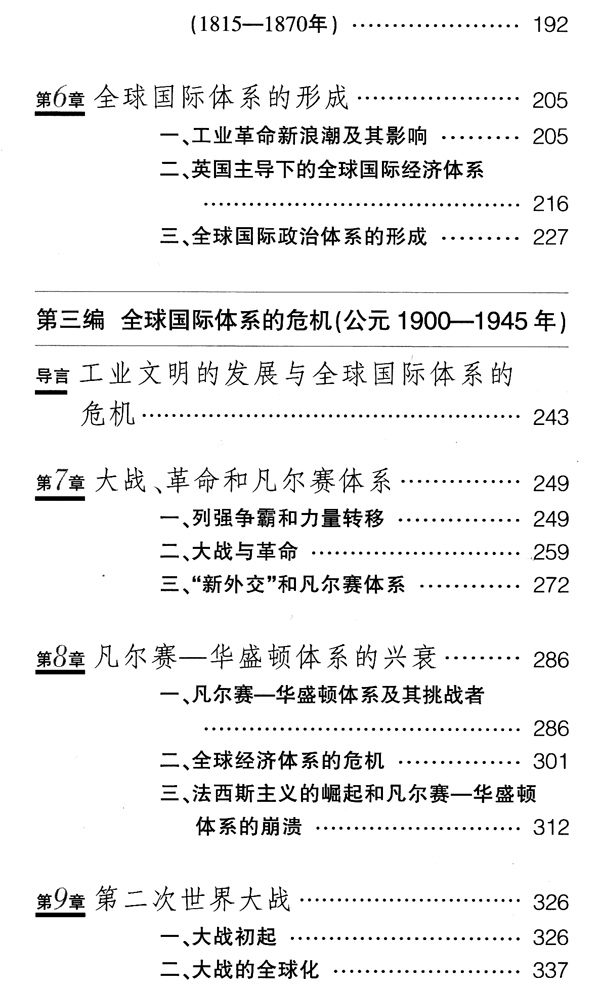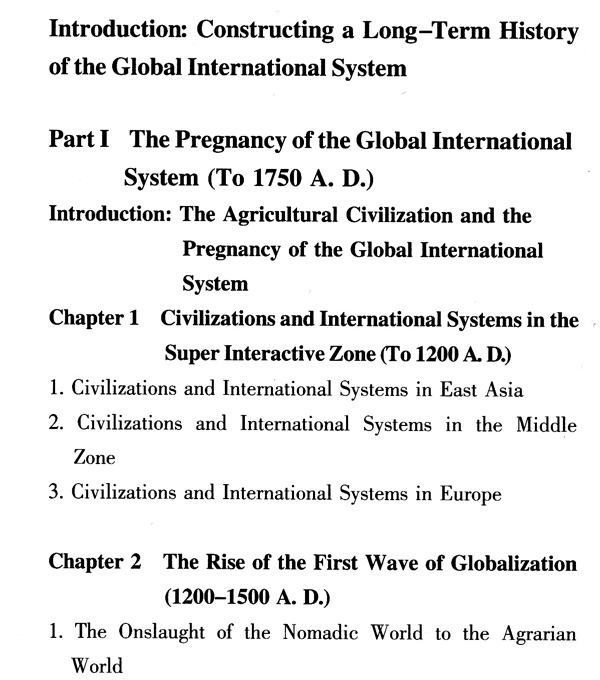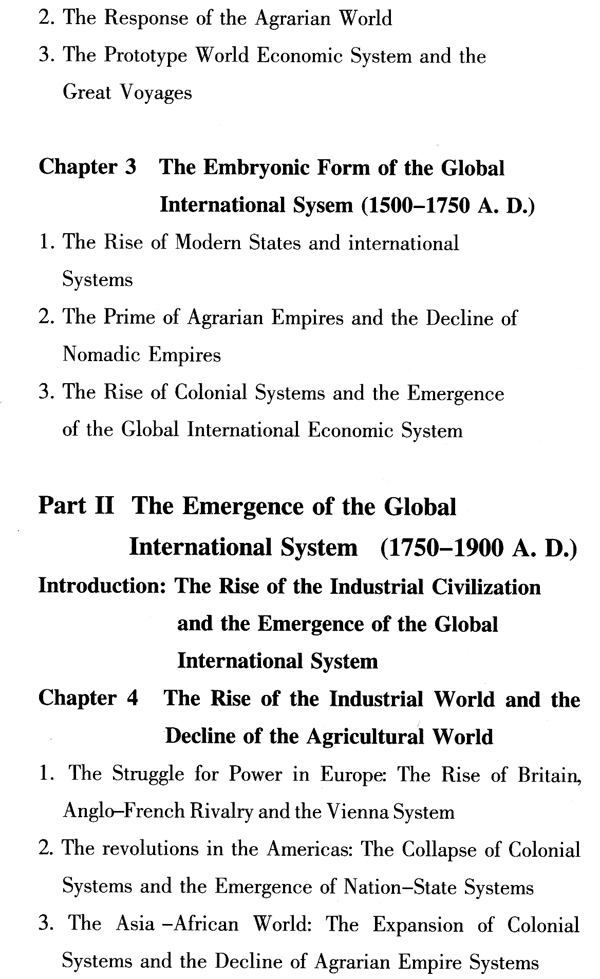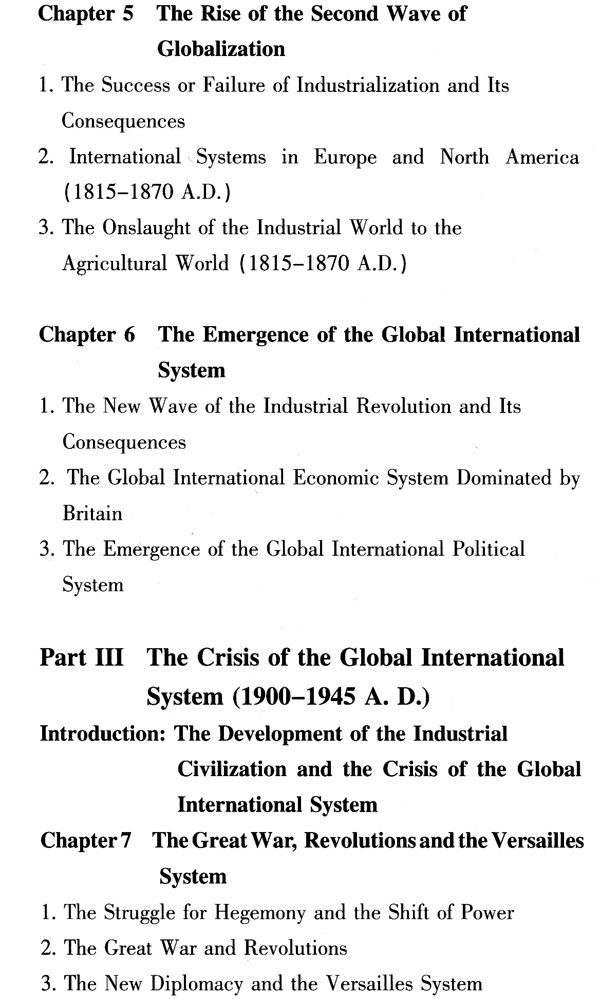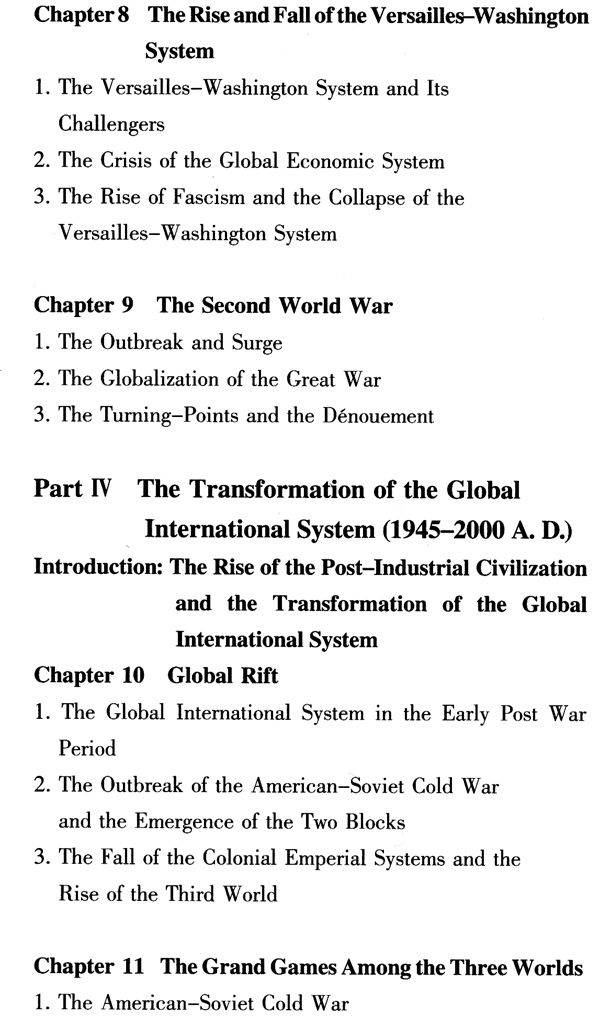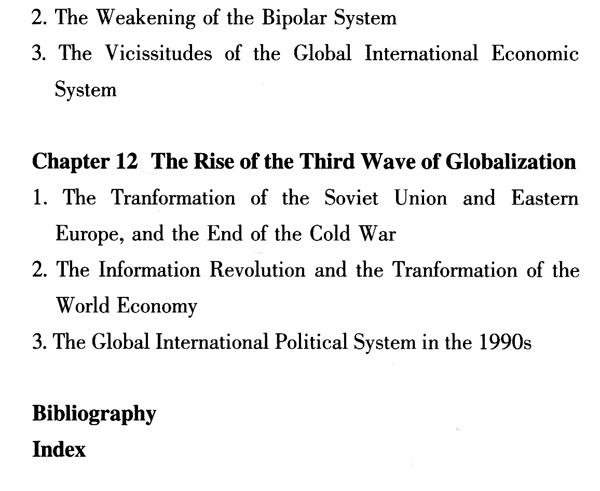《全球国际体系的演进》
2013-01-31
李春放 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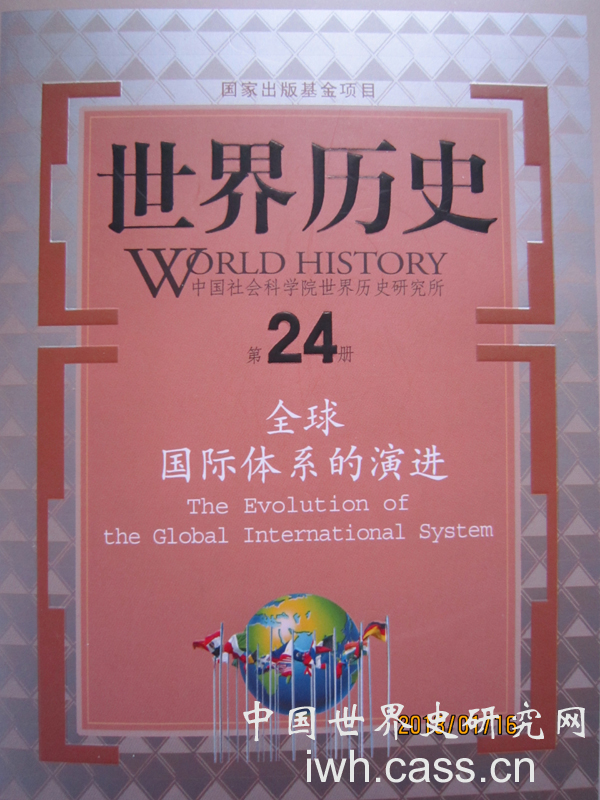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该书是《世界历史》(多卷本)第24册。
构建长时段全球国际体系史
——《全球国际体系的演进》导论
本书主要涉及世界历史中的国际关系部分,旨在叙述全球国际体系的演进。
“国际关系”顾名思义即国家间关系。国家间关系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传统的“国际关系”定义多为狭义,偏重起源于西欧的现代国家——“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结果,作为世界历史分支的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范围和内容长期受到不合理的限制,显得格外狭隘和贫乏,绝大多数所谓国际关系史著作不过是近现代外交史著作。克服这一弊端的关键是扩展视野。
如果将“国际关系”的狭义的定义从“国家”与“关系”两方面扩展,就会获致较宽泛的定义。一方面,“国家”不限于“民族国家”,而是囊括有史以来各种形态的“国家”,如城邦、王国和帝国等;另一方面,“关系”也不限于政治关系,而是包括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其他方面的国际联系与交往。广义的“国际关系”还可以涵盖国际舞台上相对独立、有较大影响力的“跨国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本书是世界史著作,故采用广义的“国际关系”定义,但笔者主要关注关键性的国际行为体,重点考察国际政治关系及作为其基础的国际经济关系。
“国际体系”也称“国际系统”。正如K. J. 霍尔斯蒂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体系可以被定义为由一些按照特定的规律相当频繁地相互作用着的政治实体——部落、城邦国家、国家或帝国——所构成的任何一种集合体。”狭义的国际体系局限于威斯特伐利亚模型,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后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而广义的国际体系则超越了这一国际体系模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发轫与国家的起源。前者的历史仅300多年,而后者的历史至少长达数千年。国际体系涵盖的地理范围可以小至两个毗邻的蕞尔城邦,也可以大至全球。“全球国际体系”指涵盖全球的国际体系。
叙述全球国际体系的演进涉及复杂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体系研究领域发展缓慢,视野狭隘,内容贫乏,难于指导史家建构世界历史中的长时段宏观国际体系史。令人欣慰的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国际关系领域的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产生了一批可供借鉴的学术成果。
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是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和系统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所谓“系统”,即“有相互作用的元素的集合”,而系统现象随处可见。贝塔朗菲指出,“系统问题本质上是针对分析方法在科学中应用的局限性问题。”分析方法“是指被研究的实体分解为结合在一起的各个部分,因此这个实体可以由合在一起的部分组成或重新组成。”但是,对系统问题而言,上述方法并不适用,因为“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换言之,“各级‘系统’不能靠研究其孤立的有关部分来了解。”与机械论观点相反,系统思想重视系统问题的整体性、动态相互作用和组织问题,后者在现代物理学和现代生物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贝塔朗菲认为,“社会科学是社会系统的科学。因此必须运用一般系统论的方法。”他强调,“社会学及其有关领域实质上是研究人类集团或系统,从家庭或工作组等小的集团,经过无数正式非正式组织的中间单位到国家、势力集团、国际关系这样的最大的单位。许多提供理论表述的尝试都是系统概念或这个领域中的某个同义语的阐述。最终人类历史问题将会是系统观点的可能的最广泛的运用。”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三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是从跨学科和系统论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次巨大冲击。沃勒斯坦认为,在研究“现代世界”社会变迁过程时,合适的分析单位应是“世界体系”,而不是“主权国家或国家社会(national society)”,“诸主权国家应看成是这单一社会系统之内诸多结构中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此外,他还“注重在某种抽象的层面上研究世界体系,即描述整个体系结构的演进”。世界体系理论成为全球化理论的重要思想先导,两者都为重新建构世界历史,尤其是国际体系史,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启示。
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是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2000年专门设计出一套理论工具,将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历史结合起来,将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结合起来,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史叙述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套理论工具由“分析层次”(levels of analysis)、“分析领域”(sectors of analysis)和“解释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三部分组成。布赞和利特尔指出,国际关系通常有五个“分析层次”,人类社会至少有五个“分析领域”。五个“分析层次”是国际体系、国际子体系、单位、子单位和个人;五个“分析领域”是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或社会文化)和环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采用层次分析或领域分析方法并非独创,只不过对层次和领域的划分、界定和偏重往往见仁见智,但“解释源”的提法颇有新意。“解释源”指解释行为的变量。“结构”(structure)、“过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三个主要的“解释源”。人们对“结构”与“过程”耳熟能详,对“互动能力”相对陌生。所谓“互动能力”,系指“单位”或“体系”内部交通、交流和组织能力的量。它涉及物品和信息传输的量、速度、距离和成本。这种能力主要取决于地理因素和技术因素。地理因素有距离和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可接近性”。这里的技术因素指广义的交流技术,它们既包括有关的“物质技术”(physical technology),如交通和通讯的设施和工具,也包括有关的“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如语言、文字、宗教、外交、货币、汇票、规则和制度等。“互动能力”不但是布赞和利特尔的理论工具的精髓,而且是洞悉国际体系演进史的奥秘的钥匙。
在本书中,笔者力图将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叙述结合起来,注意根据需要借鉴与吸收国内外学术界在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史学探索方面的最新成果。笔者的视野是全球性、宏观性和整体性的,而历史观是演进的。这种视野和历史观在许多重要方面与一般系统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并行不悖。全球化并非近期才发生的现象。本书采用全球化三次浪潮说,即15世纪发轫的大航海运动掀起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掀起了第二次全球化浪潮,20世纪后期信息革命的兴起和冷战的终结掀起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当然,大航海运动又可以归因于旧大陆的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变迁。布赞和利特尔设计的理论工具对本书颇具参考价值,尤其是其中关于“互动能力”的部分。此外,为了对全球国际体系进行长时段宏观历史描述,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阿诺德•汤因比等文明形态史学家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史学家的某些史学思想和历史著述经验。
全球国际体系经历了长期孕育、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有赖于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战争及战后的和会与和约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颇受传统国际关系史家的青睐。然而,归根结底,国际舞台上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事件不过是表象,真正塑造全球国际体系的长期决定性因素是人类的互动能力。人类互动能力的重大突破迟早会在国际体系中引起相应的变化。因此,本书包括但又不限于传统外交史的内容。在叙述某一时期的区域性或全球性国际体系时,特定文明与特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安排、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军事系统的效能都将纳入笔者的视野。
鉴于本书涉及的历史跨度大,宏观国际体系涵盖面广,国际行为体众多,且受篇幅限制,笔者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出全球国际体系演进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