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雪堂辩诬,为观堂辩诬
——罗继祖与“王国维之死”
2021-09-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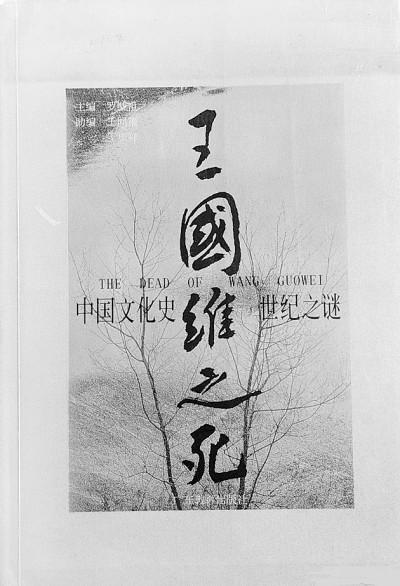
罗继祖著《王国维之死》

罗振玉(左一)、王国维(左二)等逊清朝廷官僚合影。资料图片
【述往】
学人小传
罗继祖(1913—2002),浙江上虞人。自幼在祖父罗振玉指导下治学。曾在东北博物馆、大连图书馆工作,吉林大学教授。著有《辽史校勘记》《永丰乡人行年录》《枫窗脞语》《庭闻忆略》《王国维之死》等,编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
一出生就“认识”王国维
罗继祖是罗振玉长孙,他1913年在日本京都出生时,王国维也携家眷寓居京都,所以罗继祖一出生就“认识”王国维。在日本京都生活和随罗振玉回国寓居天津期间,罗继祖都曾多接王国维音容。罗继祖说:
我五六岁就见过他,一九二三年,他应溥仪之召从上海来北京,到一九二六年这几年间,他每到天津必住在我家,我那时已经十二三岁,至今对他的声音笑貌还留有印象,中等身材,清癯面貌,唇上鬑鬑短须,头垂发辫,戴近视眼镜和瓜皮帽,系腰带,一口海宁话,一般听不大懂。一九二七年校刊《王氏遗书》时,我十五岁,《遗书》虽然还读不懂,但却参预了校字之役。(《读〈关于王国维的功过〉》,《读书》1982年第1期)
其实不是“五六岁就见过他”,而是一出生就“见”过的。罗继祖与王国维前后相识并交往的时间有七八年之久,王国维的形象留给后人的是想象,而留给罗继祖的则是印象。加上他参与校订《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其对王国维的熟悉程度确实非后来人可比。1940年罗振玉去世后,罗继祖积极参与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八种的校写以及联系印制等事,其中《后丁戊稿》即为罗继祖所编,乙丙等集也主要由其校理。罗继祖与其三姑母即罗振玉三女、王国维长媳罗孝纯也较为熟悉,与王国维子嗣似也有一定联系。
大概因为整理编辑罗振玉文集之故,罗继祖较早接触到王国维致罗振玉若干书信,最早初步整理罗振玉与王国维往返书信的应该是罗振玉本人,总数有十数册,他后将其中若干付诸装池,由五子罗福颐保存,1949年夏,罗福颐曾撰简跋,略述其经过。1963年,罗继祖即将辗转获得的160余通王国维书信辑为《观堂书札》,并交中华书局拟出版,后因故未出。“文革”结束后,罗继祖索回书札,其中118通论学书札先刊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印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1979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吴泽派人到长春罗继祖处寻访王国维遗稿,罗继祖因将《观堂书札》交付,盖吴泽拟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王国维全集·书信卷》即将罗继祖所辑悉数收入,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
1973年3月,罗继祖开始编纂罗振玉年谱《永丰乡人行年录》,1976年12月完成初稿。(参见罗继祖《台湾版〈罗雪堂先生全集〉校读记〔上〕》)起初,该稿本及过录本只是寄奉其五叔罗福颐、堂姑母罗守巽、堂姑丈周子美(罗庄之夫)等家人审正。1978年7月10日,罗继祖致信罗守巽云:“《行年录》重要在后半,如有意见,请提出。侄但据事直说,自问当无曲笔处。”(本文所引罗继祖致罗守巽信,均见于朱松龄编著《罗守巽资料选编》,2021年1月编者自印本)可见,此书以据事直书为原则。1979年九十月间交吴泽寓目,吴泽认为罗继祖用力甚深,澄清了不少问题。1979年1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致信罗继祖,表达了出版愿望。1980年年初,上海、南京两地争欲出版此书,最终此书于1980年4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缀一副书名《罗振玉年谱》。罗继祖起初主张不署撰者之名,但在出版社的要求下署了“甘孺”之名。书出版后,罗继祖寄张舜徽一册,张舜徽回信说:“极佩叙事审密,无溢美,无浮言,宣传祖德,可颂可传……”(转引自1981年1月罗继祖致罗守巽信)这个评价应该是相当高了。
因为手握很多书札等第一手材料,故《永丰乡人行年录》中即多关于罗振玉与王国维关系的叙写。此外,有些不宜写入行年录的内容,不妨在私人通信中表达。如关于王国维与罗振玉晚年交恶之事,1978年11月26日,罗继祖致信罗守巽云:
王家的事,祖父性偏急,又专听三姑一面之辞,其实王太太这人并不凶狠,不过好听钱妈等人的挑拨,三姑就受不了,以致反目。事后王家对此并无恶感,所以《录》里也不必补叙。
很显然,罗继祖对王国维与罗振玉的关系,其实有很多话要说。不过限于年谱体例,不能过于枝蔓,遂有不少谱外之谈。类似的言论其实已先见于罗继祖1978年10月22日撰成的《跋〈观堂书札〉》(刊于《读书》1982年第8期)。
追溯“逼债”说之非
罗继祖发表有关王国维死因的文章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促成他撰文的直接原因是“到目前还有人在刊物上说王静安之死不是殉清而是受罗逼债,岂不可笑”(1981年5月12日罗继祖致罗守巽信)。在罗继祖看来,王国维之死缘于罗振玉逼债之说,乃是因当时逊清朝廷的内部矛盾而杜撰出来的、出于政治目的虚妄之说,为何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有人拾此陈说?
关于王、罗晚年交恶之事,罗福颐早在1953年即撰文略述本末,惜未能发表,后来罗继祖述及此事,也大体承罗福颐之说。
关于逼债说,罗继祖至少在1982年5月2日已知郑孝胥乃始作俑者。当日他致信罗守巽说:
郑海藏以诗出名而非学者,故少为人称道,且其人不纯正,祖父与之始终不协。现知王观堂死于逼债之说,乃郑作俑,而为郭沫若等人所信,则其为人更可知,殆所谓政策策士一流。此事自不必与二姑言之,侄在《行年录》中叙说已明白,将来还有许多材料可写。
所谓“政策策士一流”,实际上揭示了逼债说背后的政治阴谋。而在《永丰乡人行年录》中,罗继祖的说法尚比较模糊:
孝纯为长子妇与继姑有违言,仆媪复从中构之。静安虽家督,而平日家政皆潘主之,己不过问,与乡人事无巨细皆过问不同。至是伯深卒,静安夫妇莅沪主丧,潘处善后或失当,孝纯诉诸乡人,乡人迁怒静安听妇言,而静安又隐忍不自剖白,乡人遽携孝纯大归。自是遂与静安情谊参商。京津虽密迩,迄静安之逝未再觌面,函札亦稀通矣。伯深服务海关,卒后恤金,乡人且不令孝纯收受。(《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
罗继祖在此处加按语:“罗、王之隙,外人不知内情致生种种猜测,有谓王女适罗被休,实则罗女适王,因婿死而大归也。静安投湖后,疑窦益启,至有谓逼债致死者。其真情虽王门子弟亦无知之者,何论外人,更何论溥仪。”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弄混王、罗两家姻亲关系,宣传逼债说,罗继祖在此予以回应。颇疑罗继祖在为乡人撰写年谱时,尚未确知逼债说之始作俑者乃是郑孝胥,因为罗继祖在言及逼债说之时,矛头除了针对溥仪,其他就是“王门子弟”了。直到1982年5月,也就是《行年录》撰成四五年后,他才知道“王观堂死于逼债之说,乃郑作俑”。罗继祖这一节文字对王、罗晚年交恶原因的剖析是中肯的,两个不同性格的人,面对同一件棘手的事情,都没有调整自己的性格,以致近三十年情谊转成参商。同样了解王、罗晚年交恶原因的王国维弟子戴家祥,即对罗继祖《行年录》中的相关说明表达了认可。罗继祖《〈观堂书札〉再跋》一文曾略引其语云:
戴教授从王登明丈手里看到《行年录》后,写信给我,说罗、王晚年失欢一事,师母潘氏即把所见所闻告诉姨甥赵万里,赵又转告我,与大作翕若合符,无偏无颇,正是史家求是态度。
作为王国维弟子,戴家祥的无疑代表了一个重要群体的态度。
王国维殉清说的坚守者
罗继祖一直坚定地持王国维之死乃殉清之说。《行年录》于丁卯年记云:
年来南势北渐,乡人与同志数辈日忧行朝,以为危于釜鱼幕燕,宜为未雨绸缪之计。顾行朝上下沓泄,人言弗恤,居恒怏怏。五月三日,静安忧愤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乡人年来与静安虽疏阔,而效忠故主之念,固信誓无贰也。“再辱”云云,自本“君辱臣死”之义。静安无遗折,殆不欲为身后乞恩计,乡人乃为代作,窃比古人尸谏,冀幸一悟……(按:遗折上,曾引起溥仪怀疑。在《我的前半生》说遗折是罗伪撰,字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手笔。此事始末,他人未必知,王门弟子则不容不知。)
这节文字包涵很多信息,而这些信息的汇合点则在逊清尸谏之说。先说遗折,罗继祖直言乃是罗振玉代王国维而作,“王门弟子则不容不知”下语很重,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罗振玉事先应该与王门弟子有过沟通,至少王门弟子当时是默认和支持了罗振玉这一行为的,因为彼此最直接的动机就是为王国维求得死后之哀荣。罗继祖提及1927年之时,他人或无感于时事变化,甚至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感到“兴高采烈”,而罗振玉及其同僚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不断的行进中,对溥仪安危的担忧,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既然可以不顾逊清朝廷与民国政府当初签订的协议,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则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对蜗居天津张园、形同“釜鱼幕燕”的溥仪,做出进一步的行为也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作为曾经的“旧臣”,自然与一般民众的关切重点不一样。罗继祖述说其祖父及一帮旧臣的忧虑,应该切合事实。但王国维的“忧愤自沉”是否也在这“同志数辈”中,却也是一个疑问。至少与王国维已经交恶的罗振玉不会在这个时候与王国维来协商行朝未来之事了。则罗继祖在这里顺着文势说到王国维的忧愤自沉,其中的关联处,交待得还是不够充分的。后来罗继祖对此说得更为详细一些。他说:
根据王先生十六字的遗嘱,再结合王先生一生言行来看,我们说王先生之死是殉清,是尸谏,推而至于陈先生赞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梁先生从各方面的分析,王先生地下有知应叹为知言……王先生之死有远因,有近因,远因应追溯到幼年在家庭里所受的封建教育和中年所研究的西洋哲学;近因呢?我认为,叶德辉之被枪毙不能说没有关系,起码使王先生在心灵上增加恐怖……梁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人,但不是革命对象,到必要时还要避一避时局风头,因而使王先生感到天津张园溥仪身边太危险了,同时也感到自身,甲子侥幸不死,这一次万难幸免了,所以决然自杀。(《〈观堂书札〉再跋》)
罗继祖联合陈寅恪、梁启超之说来集成殉清尸谏说,这里的逻辑关系尚需进一步论证,但罗继祖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晰的。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远因、近因说的分析维度,应该也大致符合一个自杀之人的常态。与《行年录》稍有不同的是:《行年录》主要从溥仪可能身陷危境而自己上言不能达,以此“忧愤自沉”;而此处所忧则不仅有溥仪,也有自己。至于说甲子“侥幸”不死云云,则还是为了合理解释“一辱”与“再辱”的关系。其实客观的情形是:甲子之变,不遑说溥仪,王国维同样也无性命之忧;北伐即至,王国维同样是安全的,甲子之变时,王国维尚身在南书房行走任上,而此时他从“组织关系”上已经与逊清朝廷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幸免”于难,其实是无需考虑的问题了。深感罗继祖此处“侥幸”二字或有失当。
王国维当然是关心溥仪的安危的,但以一个逊清朝廷局外人的身份,这种关心是否到了需要自沉以明志的地步,还是有疑问的。所谓“君辱臣死”,一般的前提是君已受辱,方才谈得上臣以赴死,岂有君尚未受辱,而先行赴死的?以当时王国维与溥仪行朝相当松散的关系,是否要走到这一步,实在是有疑问的。
要说明王国维之死是殉清,必须以王国维是忠心耿耿的遗老为前提,若“遗老”尚且不纯、不愿或不彻底,“殉清”未免就成无根之谈了。罗振玉一心以复辟清王朝为念,此已成共识,罗继祖也持此看法。但王国维是不是与罗振玉一样心甘情愿做遗老呢?学界的看法颇有差异。罗振玉、金梁、杨钟羲等遗老自然众口一词以王国维为忠诚的遗老,而遗老群体之外的人看法就不一定了。顾颉刚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就认为,王国维“他做遗老明白是他的环境逼迫成功的”,若非因得到罗振玉的种种帮助,王国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所以“大家只觉得他是一个清室的忠臣而已,这岂不是一个大冤枉”。(《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即认为:因为结识罗振玉,王国维的周边形成了以遗老为主体的群体。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厚于情谊的王国维不能自拔,便逐渐逐渐地被强迫成为了一位‘遗臣’。我想他自己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郭沫若全集》第二十卷)。1980年4月,谢国桢为《永丰乡人行年录》撰序云:“余以为雪堂老人于清末成为保皇派,犹且拖着王静安师一齐下水,误己误人,自贻伊戚。”顾颉刚、郭沫若与谢国桢都认为王国维是“被”罗振玉遗老的,“被”遗老与一心要做遗老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罗继祖则承罗振玉之说,认为他们都是典型的清朝遗老。1978年10月22日,罗继祖撰《跋〈观堂书札〉》认为:“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这一点是共同的,并不为家庭嫌隙有所动摇。”他更认为王国维成为遗老乃是其自觉的行为,并非受罗振玉引导或逼迫。他说:
有人说观堂随祖父避地日本,才使观堂走上遗老道路,这也是形式逻辑的看法,倘使当日观堂从心里不愿追随,也不会违心曲从……我认为观堂甘心作遗老决定于去日本之前,从观堂所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和他自称得意之作的壬子三诗完全可以看出。(《对王观堂的器重——〈家乘点滴〉之六》)
如果把王国维与遗老的关系分几个阶段的话:辛亥之后至寓居京都期间是第一阶段;从日本回到上海寓居时期为第二阶段;从北上出任南书房行走至去世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清亡初期,王国维在京都以若干文学作品表达了“故国之思”;第二阶段王国维从京都回到上海,与沈曾植、朱祖谋、郑孝胥等遗老过从较多;第三阶段入直南书房,则与逊清朝廷以及溥仪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并亲身经历了甲子之变。罗继祖认为王国维在去日本之前已然有遗老之心,实际上直接否定了由罗振玉影响而成为遗老的可能。罗继祖提出的依据是其《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一诗以及稍后编定的《壬子三诗》。但此《壬子三诗》正是去日本之后创作的,尚不能证明王国维在去日本之前即有遗老之心。在《壬子三诗》中,《颐和园词》以慈禧一生为中心写爱新觉罗一氏末路,《蜀道难》哀悼端方,确实对清王朝的终结寄寓了深深的哀思。狩野博士虽然任教京都大学,但因为初到京都,故在送行狩野游历欧洲时,也弥漫了一种浓重的故国之思,其中若“谈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剧可哀。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云云,也确乎蕴含着一定的遗民之思,而在铃木虎雄索阅此诗时,王国维呈上诗并致函,特别提到诗歌中对日本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忧虑,他说:“窃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国维以亡国之民为此言乎。”(王国维1912年10月7日致铃木虎雄信,见《王国维书信日记》)他直接以“亡国之民”自称。但这种遗民之思究竟是出自本心,还是来自罗振玉的影响,若无十分明确的证据,也确实不能简单就下结论。
对于谢国桢说罗振玉“拖着王静安师一齐下水”,罗继祖不能认同。他说:
据我主观认识,罗、王两人在清末这段时间对时局的看法还是很一致的,不是你东我西。从王先生性格可以说,他没有世俗猎取高官的欲望,也没有做革命投机生意的奇想,书生本色只有规行矩步地服从命运,况且回顾家世还有“安化郡王”那一段忠勇殉国的光辉历史,以及他那“我是祝陈乡后辈”的有抱负的诗句,所以跟着泛海东去,并不是受外界力量的“拖”。(《我的祖父罗振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其实不遑说清末这段时间,民国年间,王国维与罗振玉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也是基本一致的,检《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可见其大概。罗继祖对王国维性格的把握是准确的,王国维对政治有态度,但自身基本无欲望,也就是没有用行动介入其中的欲望。张勋复辟时,寓居上海的沈曾植、康有为等纷纷北上,便无一人提议带上王国维,沈曾植更是将北上之事嘱家人勿告之王国维,可见即便在遗老群体中,王国维也是基本被忽略甚至回避的一位。
罗继祖又说:
他前半生,出国留学,学洋文,研究西洋哲学,俨然是个维新开明人士。中间对仕进无意,专去研究文学和戏曲,也不失为一个想在新的学术领域里创新的学者。后半生由于时局剧烈转变,随我家东渡日本,治学方面也舍旧从新,又和溥仪搭上关系,堕落成为顽固遗老,走上反动。短短五十年而变化这么大,令人难于理解。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影响不能没有,迫胁并不存在,因为王先生并不是胸无主宰随人牵着鼻子走的人。(《〈观堂书札〉再跋》)
王国维治学范围大体经历了一个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而其政治思想也有从务新到守旧的变化,这都是可以覆检的事实。不过罗继祖在这里将王国维与溥仪建立关系与成为“顽固遗老”直接挂上钩,似乎也显得有些跳跃。但罗继祖说“王先生并不是胸无主宰随人牵着鼻子走的人”,这是深契王国维个性之言。但这种自成崖略的个性,也可能恰恰成为他“遗而不老”、有思想而乏行动的理据,可能谁也难以撼动王国维以遗老之心而自居于遗老群体边缘的状态了。
即便罗振玉家人,也并非都从殉清角度来解读王国维之死。1954年,罗福颐曾撰《忆观堂先生手札二通》(《江海学刊》1982年第2期),其中即有云:“其实观堂丈之死因,实先罹丧明之痛,后悼乱离之忧。”此文虽然发表于文章撰写后近三十年,但他对王国维死因的分析,与王国维之女王东明的看法相似,尤其是王国维之死与长子王潜明之死的关系,两人的看法彼此呼应。我觉得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同志数辈”说与逊清朝廷党争
这里再简略说说罗继祖提到的“同志数辈”的内涵,字面上当然是指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在王国维与罗振玉交恶的情况下,王国维不在“同志数辈”,大概是不言而喻的。但据实说,王国维原本是在其列的。丁戊年(1937),罗振玉撰《升文忠公〈津门疏稿〉序》言及溥仪在紫禁城时,升允密疏陈奏,“或公起草,或遣予代作,或一人具疏,或联名以闻。当道为之侧目,致以公与予为朋党,公弗顾也”。此处虽然只是言及罗振玉与升允二人,但其实下面接着说:“亡友王忠悫公受知于公,为公门人,其任南斋时二疏并附录卷末,一以志公眷眷君国,一以志当日之声应气求,如公所谓吾道不孤者,俾传之方来,不至泯灭。”(《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
王国维与升允声应气求,确乎是事实。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亦记云:
乡人与王静安先后被逊帝召直南书房,王出升吉甫荐,乡人度亦出升荐,曾面质,升坚不肯承。乡人既屡与升联名上书,逊帝师保左右嫉之甚。及逊帝出居日使馆,诸人议论纷纭。升自津扶病趋谒,赞乡人议,群遂指目为朋党,郑孝胥且悻悻南归。即逊帝莅津,租张园为行邸,时园归粤商,乡人与同直清远朱聘三汝珍共经手,某某乃藉端媒蘖,计得售,逊帝渐疏乡人。顾问之授,外示尊崇,实远之也。
这里说了溥仪身边的派系斗争问题。其实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中将张园当时的党争说得更为细致。他说:
溥仪身边大致分成三派:亲贵和内务府旧人为一派,郑、金就是从这一派里分裂出来的;以陈宝琛为首,因他是师傅最受溥仪尊敬,有一些人依附他作外围成一派,这两派人数都较多;南书房同僚温肃、杨钟羲、朱汝珍和祖父、王先生,包括柯劭忞(柯名义隶懋勤殿)为一派,这一派人少力弱。党论倾轧的结果,祖父被疏远了,派中人也受到打击。(《〈观堂书札〉再跋》)
这就是当时朝廷三组“朋党”的基本情形,而郑孝胥与金梁则是其中用力最大者。后来的情况虽然有一些新的变化,但罗振玉的劣势还是没有改变。罗继祖说:“后来张园小朝廷的权一直掌握在具体执事人胡嗣瑗、景方昶、陈曾寿几个人手里,郑孝胥和他们时分时合,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朝夕和溥仪接近,他们又都学会一套固宠弄权的手法,得到溥仪的信任,把张园弄成死水一潭,外人如何也打不进去。”(《〈观堂书札〉再跋》)升允、罗振玉与王国维三人是相对固定的“朋党”,其中升允与罗振玉要更为密切,而朱汝珍则是与罗振玉共同经手张园的人。因为他们一度深得溥仪赞赏,也因此受到其他政客的嫉妒。郑孝胥悻悻南归大概就是一种迹象了,但后来郑孝胥地位日隆,罗振玉的边缘化也就慢慢成为了现实。今检王国维与罗振玉往返信件,也颇有共疏之例。但当年的“同志”,到了1926年、1927年之交时,显然发生了转变,这也同样是一种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罗继祖关于王国维自沉的描述应该更多来自于罗振玉的自述。罗振玉在《集蓼编》中述及此事云:
乙丑以后,连年值内战,津沽甚危。予与升文忠公、王忠悫公忧之甚,然均无从致力……至丁卯,时局益危,忠悫遂以五月三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上闻之悼甚,所以饰终者至厚……一旦完大节,在公为无遗憾,而予则草间忍死,仍不得解脱世网,至此万念皆灰……(《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
罗振玉的表述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时间意识的,罗继祖以“年来”二字,将“同志数辈”的关系似乎一直延续到丁卯五月。而罗振玉则将“乙丑以后”与“丁卯”做了区分,在丁卯以前是明确的“予与升文忠公、王忠悫公”三人,而言及丁卯,则不再合说三人。但将时局与王国维之自沉直接联系起来,罗振玉与罗继祖还是一致的。罗振玉以“完大节”来定位王国维之死,则殉清之意故昭昭在焉,罗继祖承续此意,只是言说得更为详实而已。
辩诬:身份与学术的双重责任
1918年4月25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提及柯劭忞之幼子方六七岁,“颇似长孙”,罗继祖在此信下按云:“公札中谓‘颇似长孙’,乃以我为比,我小时弱不好弄,公甚喜我规行矩步,听大人话。记得我七岁返上海时,熟人见我说举止甚似三太爷(三太爷乃淮安人对公之习惯语)。公此札竟举我为典型,可见爱我之笃矣。”(《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长孙,罗继祖幼时备受罗振玉赏爱。
“这几年来,我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我祖父辩诬,同时也为王观堂先生辩诬。”(罗继祖《再为观堂辩诬》,《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辩诬应该并非罗继祖的初衷,只是对于被尘埃掩盖了很久的事实,他有一种揭示真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质实而言,罗继祖对王国维之死的看法基本上笼罩在罗振玉之说之中。但除了殉清说之外,罗继祖确实澄清了诸多谬说,其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作者:彭玉平,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