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独健:甘为人梯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家
2022-03-23
小传

翁独健(1906-1986),原名翁贤华,福建省福清市三山镇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的奠基者、领导者之一。
翁独健出生于贫寒之家,三岁时罹患小儿麻痹症,致一足跛行。但他身残志坚,自强不息,改名“独健”以自励。通过刻苦学习,他在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1935年赴美留学,193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随后游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1939年回国后,翁独健先后担任云南大学、北平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翁独健是新中国成立前著名的爱国民主教授之一,他同情革命,支持和帮助北平地下党开展了大量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翁独健担任了系列行政职务和学术职务,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委员,历任燕京大学代校长,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顾问、兼民族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历史系主任,并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会长、中亚文化研究国际协会副主席等国际国内学术团体领导职务。
翁独健深怀赤子之心,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在50年职业生涯中,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风雨同舟。1979年11月,他夙愿得偿,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翁独健治学严谨、成就卓越,为蒙元史、民族史研究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学界享有崇高声望。1986年5月,翁独健积劳成疾,猝然长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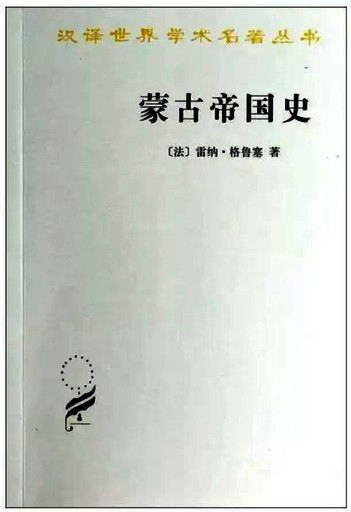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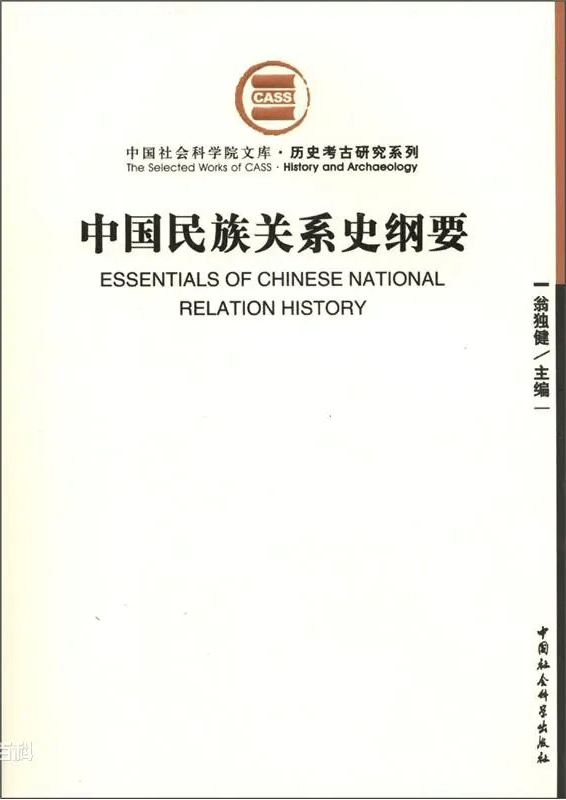
翁独健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的奠基者、领导者之一。翁独健爱党爱国,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论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论是作为同情革命的爱国民主教授,还是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他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风雨同舟、披肝沥胆、艰苦与共,体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高尚的政治品质与历史担当。
同心同德 风雨同舟
1939年,翁独健学成归国,执鞭杏坛。彼时山河破碎,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挣扎。翁独健坚守民族气节,不仅在课堂上传授中国历史知识,为赓续中华文化命脉尽心竭力,而且教育和勉励青年学生“顶天立地做人,勤勤恳恳读书”,做有人格、国格、讲气节的人,为中华民族的绵延保留思想的火种。他以身垂范,在物价飞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宁愿收入菲薄、艰难度日,也拒绝去待遇优渥的伪北大任教,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
翁独健是新中国成立前著名的爱国民主教授之一。他关心时局、忧国忧民、追求进步,不懈寻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复兴的道路。在探索救亡的道路上,他深刻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同情革命,主动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成为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朋友。1942年,翁独健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冒着巨大风险协助地下党完成各种任务,保护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抗战胜利后,翁独健执教于燕京大学,继续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政权的独裁专制,积极拥护共产党的进步主张,大力支持学生运动。据1946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的丁磐石回忆,翁独健多次和雷洁琼等思想进步的教授一起,动员燕京大学中外教授发表声明和宣言,声援学生的罢课、游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进步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和地下党小组经常借用翁独健家的客厅召开秘密会议。当时的燕京大学地下党员曲慎斋、项淳一等同志以党员的身份与翁独健保持密切往来。翁独健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当他得知丁磐石要去解放区工作的时候,对他给予殷切的勉励,并不无遗憾地说:“你去解放区好好工作吧,唉,我就是腿有残疾,行动很不方便,不然,我也去了。”北平解放前夕,翁独健在地下党组织的燕京大学护校指挥部担任总指挥,在师生中享有崇高威望。他与吴晗、张奚若等著名的民主教授一起,团结、组织燕京大学的广大爱国进步师生,为迎接新中国的曙光积蓄了力量。
北平解放后,翁独健与爱国进步知识分子一起,拥护党的领导,紧密配合党的各项工作需要,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起到“领头羊”的关键性作用。1949年8月31日,翁独健与何戍双、罗常培等12位知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感想》,表示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新中国,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和爱国群众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团结广大工人、农民,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切反动残余势力作斗争,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北平后的政权平稳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翁独健紧紧追随党的步伐,积极投身火热的新中国政权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他先后担任燕京大学代校长、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顾问,兼民族历史研究室主任和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委员,为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十年“文革”中,翁独健精神和身体上饱受摧残,不仅遭到打压,还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被分配去打扫厕所。有人戏称他为“厕所所长”。但是他没有动摇理想和信念,没有改变政治立场。被关牛棚期间,有的学者感到心灰意冷,表示以后要将自己的书籍卖掉,再也不搞学术研究,翁独健坚定地说:我还有信心,我的书一本也不丢!”之后,他重新回到科研和领导岗位,他满怀激情,迅速投入工作。1979年11月,翁独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以实际行动诠释和践行了与党同心同德、风雨同舟的初心夙愿。
严谨治学 享誉中外
翁独健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通晓多门语言,治学严谨、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特别是在蒙元史、民族史研究领域成就斐然、享誉中外。
翁独健是中国蒙元史研究的拓荒者,以扎实厚重的蒙元史研究成果,赢得国际国内学术界的景仰。早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期,他就选择了以蒙元史为主要学习领域。为国争光、立志报国,是翁独健选择蒙元史研究的直接原因。他在《我为什么学习元史》一文中说:“我对蒙元史研究有兴趣是从大学时开始的。大学一年级听陈垣先生‘中国史学评论’的著名课程,课上谈到十九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当时巴黎有几个著名汉学家;后来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汉学中心抢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垣先生鼓励我们把它抢回北京来……我们同学中,聂崇岐选择了宋史进行研究,冯家昇研究辽史,我则开始搞蒙元史研究。”在陈垣、洪业、邓之诚等史学前辈的指引下,翁独健不畏艰难,刻苦钻研,取得优异的成绩。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元田制考》、研究生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证翔实、论证严谨,获得学界好评。1935年至1939年,翁独健远渡重洋,留学欧美。他先是求学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学系,通过三年艰辛努力,用英文完成了博士论文《爱薛传研究》,获得博士学位。该文在广泛收集中外各语种史料的基础上,深入考证了13世纪下半叶蒙古汗庭中最有影响的基督教徒爱薛的事迹,至今仍然深受国际蒙元史学界的推崇。之后他到法国巴黎大学,师从国际汉学家伯希和。回国后,翁独健任教于各大高校,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展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为中国蒙元史研究赢得了国际学术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翁独健继续参与了蒙元史研究和学术组织的大量工作。他与韩儒林先生共同组织《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的翻译工作,亲自翻译了该书部分章节。另外,还组织《苏联历史纲要》中有关蒙古部分的翻译出版工作,制定《蒙古史研究十二年发展规划》,为蒙古史研究勾画了远景蓝图。他还受中华书局的委托,主持完成了点校270万字《元史》的工作,组织对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的翻译,主持拉施特《史集》和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这两部波斯史籍的译校,负责编写《蒙古族简史》、编辑《全元诗》、翻译《马可•波罗行纪注释》、校订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中译本,推动了蒙元史研究的新发展。
翁独健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理论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民族史上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系列开创性的理论。1956年,他在中央民族学院主编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上发表《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发表《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论中国民族史》(《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民族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再谈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开展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几点希望》(《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等文章,集中阐述民族史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对于什么是历史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如何收集和运用民族史研究资料、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主线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些文章发表时间前后相距30年,但是基本观点和主张一以贯之,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和阐释中国历史。翁独健的观点和主张展现出敏锐宽广的学术视野与远见卓识,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构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指引了发展方向,并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至今仍然对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翁独健既注意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又关注、吸收国际研究成果,同时非常重视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功夫。对此,他戏称“我是中西药都吃的人”。他在点校《元史》过程中,查阅了200多个不同版本,共出校勘记2600余条,可谓“一字之订千滴汗”,为学界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元史》点校版本,为中华文化典籍的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高度重视收集资料,强调要“竭泽而渔”,求真求实,言必有据,反对缺乏资料基础的空谈。他淡泊名利、勤于治学、手不释卷,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但问耕耘斋”,寓意为学术研究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在生活上,翁独健随遇而安,十分简朴,却嗜书如命。在他的书房里,收藏了各种文字、各种版本和时代的专业书籍,琳琅满目,堆积如山。正是由于严谨治学、勤于探索、淡泊名利的精神,翁独健在史学研究特别是蒙元史、民族史领域成就卓著,成为一代宗师。
精心擘画 开创新局
翁独健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的奠基人、掌舵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满怀对新中国的热爱,积极响应时代号召,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长期担任中国民族史学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呕心沥血、披荆斩棘、精心擘画,开创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的新局面、新气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翁独健作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的奠基人,为民族史学科的组织、规划,特别是人才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1952年,翁独健受命担任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主任,彼时中央民族学院刚刚成立一年,正是组建教学科研队伍的关键时期。1956年,翁独健又受命担任了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同年,翁独健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代表,参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制定,对十二年内民族史研究方案提出了具体建议。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翁独健担任副所长,分管民族历史研究工作,兼任民族历史研究室主任。1961年,他与吴晗、翦伯赞等发起成立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多次组织有关民族史重大课题的学术讨论,对新中国民族史学科队伍建设、学科发展规划起到了领导、规划的重要作用。在翁独健和吴晗、翦伯赞、白寿彝、王锺翰等著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传承有序的人才梯队,开展了系列学科理论探讨和创建工作。在此期间,以民族识别工作为基础,新中国组织开展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为中心,翁独健作为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对调查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领导、组织和学术指导作用,并亲自负责内蒙古、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工作,为党和国家制定实施民族政策、推行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中国民族史学科奠定了人才队伍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学术资料,为最终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五种丛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翁独健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民族史学科的掌舵人,为新时期民族史学科的发展、规划付出了大量心血,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结束后,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民族史学界需要一位深孚众望、德才兼备的掌舵人。他不顾年老体衰,慨然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新使命,争分夺秒,竭尽全力引领民族史学科的发展,为新时期民族史学科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78年3月,翁独健作为召集人,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民族历史科学规划座谈会,初拟了《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民族历史研究规划》,为新时期民族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9年4月,在云南昆明召开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翁独健主持制定了《中国民族史研究规划草案》,并在会议上对中国民族史研究提出十个建议,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他还担任国家“六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主编,为这部著作倾注大量心血。翁独健离世四年后,该书于1990年正式出版,多次荣获国家级优秀科研成果奖项,深得学界好评,多次再版,至今仍被视为教科书级的经典著作。
翁独健非常重视学术交流。在这一时期,由于他的倡议、推动和影响,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元史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史学会先后成立,翁独健分别担任这些学术社团的会长、荣誉会长或者荣誉理事,为团结和凝聚民族史学界科研力量、促进国内学术交流、培养青年人才、推动民族史教学科研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81年5月,翁独健与白寿彝、牙含章等著名学者共同发起“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会议在北京香山召开,来自20个省、市、自治区的130多位科研教学人员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议围绕“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研讨,形成共识,为新时期中国民族史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还非常重视国际学术交流。1979年后,他多次赴国外讲学或者参加学术会议,先后去法国巴黎参加中亚文化国际研究协会理事会,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讲学,重访哈佛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去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参加中亚文化国际研究协会理事会和学术研讨会。他与国际学术界同行保持密切的学术联系,直到生命最后一天,他还在为接待日本学者来访而操劳,真正做到了为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饮水思源,今天中国民族史研究事业的每一个成就,无不饱含着翁独健的心血和期望!
春风化雨 甘为人梯
翁独健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是莘莘学子的良师益友。自1939年回国,在此后将近50年的执教生涯中,他始终教书育人、奖掖后学、呕心沥血、春风化雨、甘为人梯,为青年学子指引人生方向和学术道路,特别是为新中国蒙元史、民族史研究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推动了学术研究的传承和发展,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翁独健归国后,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北平中国大学,开设历史学及相关课程,如史学入门、中西交通史、世界史、蒙元史、辽金史、亚洲史、俄国史、中亚历史语言研究、中西文化关系史、史学方法等。翁独健知识渊博,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深受学生欢迎。据当年在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回忆,他上课的时候,不但教室里座无虚席,而且走廊和窗台上都站满了听课的学生。他在讲课中总是尽量收集新史实、新成果、新观点,并毫无保留地向学生传授自己的研究心得,指导学生如何开展专业研究,使学生大为获益。翁独健在课堂上不仅传授历史专业知识,而且向学生传播爱国进步思想,鼓励学生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他爱护学生,在进步学生遭到通缉、搜捕的危急时刻,他奋不顾身,尽全力保护学生。1948年8月,六七百名国民党反动军警特务封锁了燕京大学,要求进校搜捕进步学生。当时有人提议,让一两个情节较轻的被通缉学生出来自首,借此解除对学校的封锁,好让其余被通缉的学生脱身。翁独健听说后坚决反对。后来,在翁独健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等进步教授的共同努力下,被通缉的燕京大学进步学生全部转危为安。
新中国成立后,翁独健调任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兼民族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主任,培养了大批蒙元史、民族史专业人才。从1963年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开始,翁独健前后共招收十届研究生。他们大部分在蒙元史、民族史领域学有所成,成就突出,成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其中,成就特别突出的有姚大力、刘迎胜、罗贤佑、薄音湖、任崇岳、郝时远等知名学者。还有不少学者虽然不是翁独健的亲炙弟子,但受到过他的亲自指导栽培,对他执立弟子之礼,如芈一支、林幹、周清澍、亦邻真等知名学者。他对青年学子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凡是接受过他教导的学子,无不对他的学识渊博、为人正派、和蔼可亲、宽厚包容留下深刻印象。据罗贤佑回忆,翁独健谈锋甚健,又循循善诱,使人如坐春风。他对学生生活关怀备至,对学业严格要求。有一次,学生们想凭借他的威望,请他写一封帮助发表论文的推荐信。翁独健严肃表示,发文章要靠质量,不能靠人情,最终没有写推荐信。翁独健对学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不正之风十分愤慨。薄音湖深情回忆往事,他说:“先生对剽窃他人成果的恶劣学风深恶痛绝”,面对剽窃成果的事件,翁独健“用最激烈的言辞大声地斥责这种卑劣的行径,说这种人做人都做不好,谈何做文章!”他的言传身教对学界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他对学生的研究工作非常关心,勉励有加。据郝时远回忆,他第一次与翁独健谈起研究工作时,很犹豫地谈到蒙元时期的高丽问题,认为这个选题虽然很有研究意义,但是心存顾虑。翁独健说:“我支持你搞这个课题,思想要放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郝时远最终完成了《金元之际的蒙古与高丽》一文并公开发表。此外,在蒙元史、民族史研究领域和翁独健工作过的单位,大批中青年学者受到他的指点、提携,对他满怀仰慕感恩之情。
由于翁独健的指导教诲、无私奉献,当前,蒙元史、民族史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一支实力雄厚、传承有序的教学科研队伍。在他当年悉心培养、指导的青年学子以及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传人中,不少人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各个教学科研岗位的骨干力量,真正实现了薪火相传,桃李满天下。
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
长期忘我的工作侵蚀了翁独健的健康,使他积劳成疾,晚年疾病缠身。但他仍然顽强地与病魔斗争,争分夺秒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1986年5月28日,翁独健在一天的忙碌工作后,因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而溘然长逝,永别了深爱他的家人、师友、同事,永别了他钟爱的事业。
哲人斯逝,风范永存。翁独健留给后人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他矢志不渝地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一息尚存,奋斗不止。他重情重义,在“文革”期间,对萧乾、王锺翰等落难旧友不离不弃,不顾个人安危,为他们挺身而出,施以援手,展现了淳朴的道义担当,用行动诠释了人间真情,在士林传为佳话。他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对某些人借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打击历史学家吴晗的恶劣行径给予义正词严地揭露和驳斥,展现了一位史学家和爱国知识分子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高尚人格,令人肃然起敬。他自强不息、努力拼搏的奋斗精神,追求真理、坚持原则的高尚情操,一丝不苟、求真求实的严谨学风,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人生境界,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正直无私的高洁人品,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和发扬。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斯人已逝,但翁独健的事迹和精神将代代相传,以至无穷。
(作者:彭丰文,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