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宽行:至简人生 深情于学
2023-0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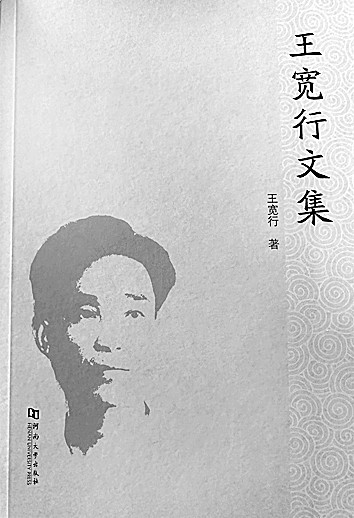
作者供图

王宽行(右一)与友人在一起,左一为张如法。作者供图
【述往】
学人小传
王宽行,1924年出生,2004年去世,江苏邳县(今邳州市)人。1948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9年1月至1950年9月休学,1950年9月到1952年7月在无锡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学习,1952年9月至1953年7月在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读本科,毕业后分配到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今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著有《王宽行文集》。
一
1965年高中毕业时,我报考了清华大学土木建筑专业,可考前学校分别召集不同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开会布置报考志愿的消息,让我有了不祥之感。果然,虽然我的成绩完全合格,最终却落榜了。
1977年,停顿多年的高考恢复了,对一直心心念念想上大学的我来说,真是一次历史性机遇,然而,我只能无奈再度止步:未能报上名。1977年高考只允许1966、1967、19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报考,如我这样1965年参加过高考未被录取的考生是不允许报名的。不久后,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考研的年龄上限放宽了,而且对于有专业特长和研究才能的在职职工,报考时不受学历限制。我马上明白,这是我读大学的唯一机会了!作为理工男的我,立即自学大学文科课程参加考研,原因很简单,自学理工科无异于“自杀”。
1979年9月,34岁的我,历经了14年小学、中学教书生涯后,考上了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即今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师从王宽行先生,成为宽行师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
面试时第一次见到浓眉大眼、心直口快的宽行师,他爽朗的笑声时时回响在严肃的复试场上。看得出,在座的高文教授(1908—2000年)、华钟彦教授(1906—1988年)等老一代学者都非常欣赏宽行师。面试时,华先生问我:荀子是法家还是儒家?为什么?我回答完后,华先生做了点评。宽行师和华先生为此题还有一场小小的辩论,让严肃的考场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毕业留校后,我参加过多次研究生面试,罕见此种景象。
后来我才知道,宽行师新中国成立前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无锡国专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张亮丽的名片,“培养的学生绝对数量不多,但却保持了极高的成才率”,有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学者将其与北京大学等名校并称。1953年宽行师毕业时,该校已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他由江苏师院分配到开封师院工作。宽行师和系里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关系如此融洽,是因为宽行师学问扎实、见解独到而又为人耿直,为中文系的老先生们所认可。
第二次见到宽行师已是开学后,地点是宽行师的家,校内排房中的一间(那些排房现在已经拆除,改建为河南大学开封明伦校区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当时开封师院中文系许多老师都住在这些平房里。尽管我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宽行师家的简陋仍然令我大为吃惊:全部家当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破旧的三斗桌,几个小书架和一些放在地上的炊具。
我没有在开封师院读过本科,可我对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并不陌生。1974年到1976年的这三年,我一直在开封师院历史系“工作”。那时,开封空分设备厂“工人理论组”和开封师院历史系共同承担《王安石诗文选注》的工作,我是空分厂“工人理论组”向空分厂中学借调的高中语文教师。因此,我隔三岔五地要从历史系去开封师院的教授院(河南大学金明校区南门外教授院,现已拆除)拜访中文系高文教授,请他审阅我撰写的初稿。与教授院的住房相比,宽行师的住所实在是太简陋了。这种简陋不仅表现在房屋的面积和结构上,而且表现在室内的家具上。
作为青年教师,宽行师与当时的开封师院教授相比,工资待遇相差悬殊。加上师母为农村户口,孩子均在农村,经济的重担让像宽行师这样“一头沉”(特指夫人系农村户口者)的高校教师经济一直很拮据,甚至负债累累。
宽行师一人独居开封26年,直到1979年,师母和小儿子才办完“农转非”(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来到宽行师身边,实现了家庭的初步团聚,当年的青年教师已成了年近六旬的老人。他的长子1978年考上徐州师范学院,毕业后进入邳县县中教书,直至退休。次子1982年到商丘一所中学当老师,后调入河南大学图书馆。唯一的女儿,因为已婚嫁,不能再办“农转非”,一直留在江苏农村。
师母和小儿子的到来,给宽行师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欢乐。伴随着师母的到来,20世纪80年代,宽行师告别了平房,搬进了今河南大学明伦校区西门外的家属楼,直到仙逝。在今天看来,宽行师的新居既不宽敞也不豪华,书房仍然只有几个简陋的小书架,一张结实无华的三斗桌,以及一把修补了多次的旧藤椅。我每次到宽行师家中问学,他都是坐在那把破旧的藤椅上谈笑风生。
宽行师的穿戴也相当简单,一套灰色的中山装是他的标配。从我入校至宽行师去世的25年,他一直穿着同样颜色、同样款式的中山装,无论在家中,还是在课堂上。作为长子,宽行师要照顾在老家的两个弟弟,作为丈夫和父亲,宽行师要负担妻子和三男一女的生活,因此他自奉甚俭,常年不添置新衣。据说宽行师曾订做过一套米黄色的中山装,只有出席重要会议或拜访前辈、亲友时才舍得穿。
宽行师的忘年交、河南大学文学院张如法教授在他个人博客上写道:“‘文革’前毕业的开封师院中文系学生,回忆在母校的学习生活时,都要赞美宽行兄讲课的魅力。如曾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院长的孙荪(孙广举)在《河南大学学报》上撰文说,王宽行老师讲课气势恢宏、情感激越。‘文革’后七八十年代的学生,也对宽行兄的讲课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就是先旁听宽行兄的讲课,心生敬慕之情,最终下决心考上中文系的。”张如法教授还摘录了那篇文章的片段:“我待了一星期,一天不落地听课,真是大开了眼界。印象极深的是王宽行老师讲《孔雀东南飞》,开篇两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讲了两个学时,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一唱一咏,手舞足蹈;轻音时,地可听针;豪唱时,晴空霹雳。你的思绪被他调遣,时而泣,继而涕,时而乐,继而笑,时而探首侧耳听山泉叮咚,继而仰天排胸啸大江东去,那是一场难忘的艺术享受。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天,我便要返乡了。我萌生了强烈的上大学的念头。”
二
住得简陋,穿得简单,但是,宽行师却有着一颗“精致的大脑”。这颗“精致的大脑”以善于深刻的分析著称于学界。他是开封师院中文系著名的雄辩家,讲课、发言一向以深刻著称。
在我三年读研期间,宽行师给我讲《史记》,讲汉魏六朝乐府,讲《论语》《孟子》,讲唐诗。特别是一些名家名篇,宽行师讲起来声如洪钟,每每拍案而起。屋中只有我们师生二人,宽行师讲课的气势、声音,丝毫没有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课而与他面对数百学生时有任何差别,大气磅礴,挥洒自如,激情四射。
张如法教授曾写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记述宽行师讲课时的情境,他(指宽行师)往往“先在黑板上简要写出两种观点让同学思考,然后用粉笔在第一种观点上打个大×。那时课堂上允许抽烟,他又有烟瘾,便掏出香烟点上一支猛吸一口,嗵、嗵、嗵,从讲台下来直走到教室后边,又折回来,嗵、嗵、嗵,登上讲台,拿起粉笔在第二种观点上一边打×,一边高声说道:‘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同学们显出惊讶的神色,他于是非常自信地说道:请听听我的正确观点和具体解析。”
宽行师做研究和他讲课一样,非常看重细读文本。一次谈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中“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颂诗书”,宽行师告诉我:一定不能理解成为这是写刘兰芝能干!这是写封建礼教的教育!下文写兰芝回家,刘母的“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就将“十六颂诗书”改为“十六知礼仪”,可见,“颂诗书”是为了“知礼仪”。宽行师此类耳提面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宽行师给我讲《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时,对《鸿门宴》开篇的“项王大怒”中“大怒”二字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大怒”二字表现了项羽的政治幼稚,表现了项羽入关后没有认识到刘邦已经由昔日战友演变为今日对手的重大转折。因此,项羽的政治幼稚成为解读《鸿门宴》的一把金钥匙。我在《百家讲坛》讲项羽,主要讲了项羽失败的三大原因——政治幼稚、军事被动、性格缺陷。这些认识都是我在宽行师“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在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再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宽行师非常看重“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两句。他认为:“世”是什么样的“世”,“我”是什么样的“我”,“世”与“我”如何“相违”,这是解读陶渊明归隐的关键。讲清楚了这两句,整个陶渊明的归隐就迎刃而解了。
可见,宽行师具有文本解读的非凡功力。这种功力不局限于解读文本,而且还能够通过解读文本解读作家。这是宽行师的独门绝活!细读文本,成了我此后数十年教学和研究的基本功,也成就了我在研究中的多项重要发现。
三
宽行师最钟爱的研究课题有两个:一个是陶渊明研究,另一个是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宽行师见解深刻的特点在他的陶渊明研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宽行师的研究兴趣,让他很快就有了参与全国陶渊明研究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陶渊明研究一直存在较大分歧。
1953年,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李长之撰写的《陶渊明传论》出版。此书力主陶渊明受曾祖陶侃、外祖父孟嘉的影响,并不尊崇东晋王朝,“反映了没落的士族意识”。
1954年,阎简弼撰写文章《读〈陶渊明传论〉》,批驳李长之对陶渊明的指责和否定,基本肯定陶渊明倾向人民,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
多数专家肯定陶渊明的积极一面,认为他“躬耕自资”,侍弄桑麻禾黍,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与农民有深厚情感,在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盛行的晋代,殊为难得。
1958年,陈翔鹤主编的《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陶渊明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立即吸引了中国古代文学界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
这场讨论始于1958年12月21日《文学遗产》第240期发表的3篇评陶文章,止于1960年1月3日第294期发表的1篇评陶文章,历时一年余。讨论结束后,《文学遗产》副刊选编了《陶渊明讨论集》(以下简称《讨论集》)作为总结,并由中华书局1961年5月出版。
《讨论集·前言》介绍,从《文学遗产》第240期发表第一批讨论文章起,至1960年3月底止,共收到有关陶渊明的讨论文章251篇。入选《讨论集》的有正文27篇,附录3篇,计30篇。
在这30篇文章中,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仅21篇。此21篇发表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者17篇,寄往《文学遗产》副刊未发表最终收入《讨论集》者3篇,发表在其他刊物收入《讨论集》者1篇。王宽行《从辞官归隐看陶渊明》一文是未能在《文学遗产》副刊发表却最终收入《讨论集》的3篇论文之一。
宽行师撰写此文时,36岁。在全国投稿的251篇文章中,能获得出线权,特别是投稿时未刊载,最终能收入《讨论集》,殊为不易。这一切皆缘于他对陶渊明深刻、独到的见解,也表明他的见解在当时已处于时代的前沿。即使在今天,我重读此文,仍然可以感受到内心的悸动。
宽行师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发表文章并非偶然。他1953年分配到开封师院,1954年便在《人民文学》3月号发表与权威商榷的文章《关于对〈诗经·将仲子〉一诗的看法》。在专业期刊极其稀缺、专家教授投稿亦不容易被采用的当时,宽行师的科研实力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
张如法教授生前曾回忆他初识宽行师的一个细节:“我于1959年7月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8月被分配到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由于宽行兄在古代文学教研室,我在现代文学教研室,他又长我14岁,所以比较陌生。引起我对他注意的,是系里为提高我们这批新教师的学识水平制定的一个系列讲座。担任导师的有李嘉言、华钟彦、高文、万曼等著名教授,后面赫然有一讲师职称者,此人就是王宽行。人皆有好奇心,我们一些外校毕业的新教师,听说好些教授、副教授都不能为我们开讲座,为何独独这位讲师能名列导师其列?其是‘何方神仙’?有何‘法道’?经过打听,这才知道王宽行的学术功力非凡。”
我们评价一位学人,往往有两种模式:一是看他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认为级别越高的刊物,作者的水平就越高;二是看他的代表作处于什么水平,达到什么高度,这就是代表作评价制。两种评价模式各有利弊。刊物级别高,不等于其所发表的文章都是最高水平文章,也不等于其作者都是最高水平的研究者。刊物和刊发的文章之间可能会有不完全协调之处。代表作评价制,是通过一位研究者的代表作,判断他的实际研究能力和他的研究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如果以代表作评价制衡量宽行师的陶渊明研究,他可算是一位被学界长期低估的学者。
宽行师的陶渊明研究不仅有《讨论集》收录的《从辞官归隐看陶渊明》,还有收入他个人文集的《试论陶渊明的“质性自然”》《也谈陶渊明的化迁思想与审美创造》《也谈陶渊明的政治倾向》《谈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这些评陶文章,如《从辞官归隐看陶渊明》一样,达到了那个时代评陶文章的较高水平。
在宽行师留下来的不多的遗作中,有5篇同样具有很高水平的陶渊明研究文章,足以说明宽行师对陶渊明研究的钟情。
宽行师的遗作篇数不多,特别是先秦儒家思想研究领域保留下来的文章甚少,这本是宽行师为研究生讲得最多的话题,他自己极少写成文章,而是毫无保留地讲给了自己的研究生,不少观点被他的学生写成论文发表了。为什么一位以雄辩著称的先生著述不多呢?“述而不作”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宽行师那一代人。
宽行师遗作的一个特点是以解析作品为主。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大学的许多院系或独立成校,或并入他校,自己则降格为开封师范学院。既然名为“师范学院”,培养中学教师便成了这所大学最重要的任务。中文系负责培养全省的中学语文教师,自然要给中学语文教师讲中学教材,这种“生存状况”导致了大量作品讲析文章占据了宽行师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解读古诗文名篇最见文学史家的功力,几乎所有名家都在这方面下过大功夫。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汇集北大名家林庚先生的多篇文章,选编为《诗的活力与新原质》一书(生活书店2022年版),其中专辟《谈诗稿》一章,收录了林庚先生讲读16篇作品的文章,如《君子于役》《易水歌》《青青河畔草》《步出城东门》《漫谈庾信〈昭君辞应诏〉》《秦时明月汉时关》《谈孟浩然〈过故人庄〉》等。这就不难理解宽行师的文集中为何有不少名作解读的文章。
虽著述不丰,但成文极有分量,朴实无华的文字后面,难掩一代学人的风采。虽然,宽行师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独到见解已经百不存一了,但是读者从这些有限的存世之作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位独具只眼的学者的锐利眼光。这种眼光是永恒的,这就是宽行师学术生命的价值所在。学术永远不以量取胜,代表性文章是体现一位学者真正价值的标志。
四
宽行师是一位尊师重道的长者,是一位具有文人风骨的学者。他和他的老师吴奔星先生、廖序东先生的友谊令人动容。
吴奔星、廖序东两位先生是宽行师在无锡国专时的老师。吴先生是诗人兼学者,廖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廖序东先生与黄伯荣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是国内高校应用最广的现代汉语教材。宽行师几乎每年寒暑假回江苏老家时,都要到徐州师范学院看望两位老师。一次吃饭时,吴先生对宽行师说:“让秉辰(宽行师长子,时在徐州师院中文系读本科)过来一块儿吃,来跟他吴伯伯说说话。”宽行师当即就说:“绝不能这样称呼!您是我的恩师,永远不能变。”宽行师在无锡国专上学时,吴先生讲授现代文学课。一次上课时,有学生要求吴先生讲讲《孟子》,吴先生对学生说:“若是讲《孟子》,可以请王宽行讲,有关《孟子》的学问是他的专长。”
一次,宽行师因有急事,回老家时路过徐州而未下车。吴先生再次见到宽行师责怪道:“我都奇了怪了,你工作在河南,家在邳县,徐州是你飞过去的?”师生之间的眷眷深情流淌在吴奔星先生对宽行师的责问之中,读之令人泪目。
吴奔星先生的儿子在张如法教授的博客上留言:“宽行先生尊师重道,我最有感受。他是家父在江苏师范学院的老学生,年龄只比家父小11岁,但每次来看望家父,都是毕恭毕敬,对我总是称‘心海弟’。记得宽行先生最后一次到南京看望家父,是2000年,当时犬子上小学,家父让他喊宽行先生‘爷爷’,宽行先生大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心海是小老弟,心海的孩子,就是我的侄子!’后来,宽行先生还专门给我儿子买了一支英雄牌的钢笔。”“家父卧病后,宽行先生经常电话问安,前后有十多次。起初,父亲还能够接听电话,听到宽行先生的声音,就很激动。在这里,不能不提一句,曾经的很多座上客,在家父卧病后,就再没有了音信,但宽行先生,基本是一个月打一次电话询问病情。古人云:学贵得师,亦贵得友。信乎!”
我留校后,宽行师经常到我家小坐,每次都要谈到陶渊明研究,并邀请我和他一块儿从事该项研究。由于我当时已有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答应完成手中的课题后再和宽行师合作,可我的课题一个接一个,始终没有来得及和宽行师合作进行陶渊明研究。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去看他,他仍然兴致勃勃地和我商讨陶渊明研究,可惜我最终未能实现宽行师的愿望。“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悲夫!
回首当年和宽行师促膝交谈的时光,虽历历在目,但俱成往事,不胜嘘唏。
(作者:王立群,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