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健康:正确评析奥拉比改良运动
——再读杨灏城先生所著《埃及近代史》
2022-06-20
时光飞逝,转瞬之间,我已然是上了岁数的人,怀旧的心绪越来越浓。高中那段岁月的记忆,或隐或显,时时萦绕脑海。我们上吴老师的政治课,大家都爱听,因为他把复杂深奥的哲学问题,化解成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故事来讲述。考试的论述题,印象比较深的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新出现的事物是新事物吗?”最近读了一些关于殖民主义时期埃及历史方面的英文和阿拉伯文图书,在此基础上重读杨灏城先生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埃及近代史》,感触颇深。于是我便回想起“新出现的事物是新事物吗”这个高中生必须回答的老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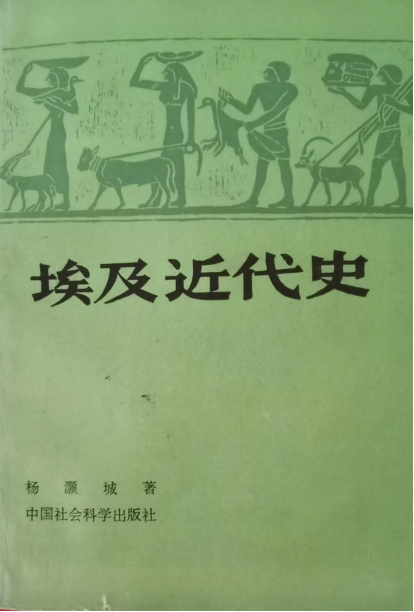
杨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埃及史专家。1957~1962年,他公派到开罗大学文学院留学,亲历和享受了纳赛尔社会主义。他曾经微笑着对我说:“小毕呀,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时,我在埃及留学,没有饿肚皮。那个时候,纳赛尔在埃及实行免费教育,我在开罗大学食宿免费,吃得好,睡得香。”这话听起来很轻松,但是杨先生创作《埃及近代史》并没有那么轻松,其用心用力与该著的学术价值,值得体会和品鉴。
众所周知,“文革”十年内乱,冲击了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杨先生的研究也受到影响。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杨先生痛惜过去耽误的宝贵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如饥似渴地觅书、读书、思索、探究。为了收集文献资料,恢复学术交流和联系,先生屈驾以排球教练翻译的身份,重返金字塔国度,再饮尼罗河水。1985年,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埃及近代史》付梓。埃及近代史,始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止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杨先生这部25万字的学术著作,构建了埃及近代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至今依然闪耀着学术之光和智慧洞见。
我说《埃及近代史》“至今依然闪耀着学术之光和智慧洞见”,某些读者可能心生怀疑,在心中暗自认为我在溢美先生。这种疑虑情有可原,毕竟先生是我的恩师,是我从事中东非洲史研究的引路人。为了消除读者的疑惑,我以埃及1876~1882年奥拉比运动(艾哈迈德•奥拉比,1841~1911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为例,结合埃及学者和西方学者的主要观点,说明先生关于奥拉比运动的基本观点,展示其论析奥拉比运动的逻辑链条,让读者自己品鉴,判断各方立场,比较孰高孰低。
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是埃及近代极为活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有“民族教授”之誉。1911年艾哈迈德•奥拉比去世时,赛义德对奥拉比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反叛平静的赫底威(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实际统治埃及的执政者,1867年从宗主国奥斯曼帝国获得“赫底威”称号)不符合民族的公共利益。”认为奥拉比对埃及民族强弱状况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对他的军队与英国军队的差距很无知。“所有这一切(指军事上的错误),都是第一个错误即革命的错误的延续。”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挑战殖民主义和限制赫底威的权力,革命的失败造成强大的外国势力的干预,对埃及和埃及人民而言妨碍了国内发展进程,还造成埃及人分裂为奥拉比派、陶菲克派和地方投机分子。赛义德对奥拉比革命的批判和对奥拉比的挑剔,显而易见是其立场决定的。
阿里•丁•赫拉勒是埃及著名的政治学家,曾经担任开罗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1999年进入埃及内阁,担任埃及青年部长。他在1999年出版的阿拉伯文版专著《埃及政治发展(1803~1999年)》中,把奥拉比运动称为“奥拉比革命”,但只简略叙述运动过程,不持立场,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阿卜杜•阿吉姆•拉姆丹是埃及著名历史学家,他1995年出版的阿拉伯文版《阿卜杜•纳赛尔之前的埃及》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奥拉比革命”。拉姆丹概述了1881年9月9日兵谏中,以奥拉比为首的埃及军队代表埃及民族提出的三点要求,指出奥拉比运动过程中军队与立宪领袖之间的合作与分裂,认为1882年5月28日奥拉比对埃及统治者赫底威发动圣战的呼吁,为7月11日开始的英国干预创造了条件。
大名鼎鼎的研究埃及民族运动史的专家阿卜杜•拉赫曼•拉斐伊(1889~1966年),是第一个把奥拉比运动称为“奥拉比革命”的埃及历史学家。他竭力客观公正地研究和叙述历史事实,指责赫底威陶菲克(1879~1892年在位)为殖民势力的爪牙和祖国的敌人,引狼入室,借外国人之手压迫自己的国民,方便殖民势力对国家的占领。他在阿拉伯文版《奥拉比革命与英国的占领》(1983年第4版)中,全面深入地论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殖民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论析了奥拉比的性格特征、所接受的教育及其作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分析了奥拉比革命失败的内因和外因,把埃及的奥拉比运动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克罗默勋爵(1841~1917年)本名埃夫林•巴林,1883~1907年间担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和总领事,实际统治埃及24年之久,人称“东方暴君”,自诩为“埃及通”。这位狂妄自大,固执而充满偏见的英国殖民爪牙,把埃及人视为“半文明的人民”。他在1904年向英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奥拉比革命”是具有高尚目标的民族革命。1908年,他出版了2卷本英文版《现代埃及》,采用传统的历史叙述话语,立场隐而不显,文笔老道。该书第2部分题目为“奥拉比反叛”(the Arabi Revolt),他把1881年9月9日奥拉比领导的兵谏诬称为“兵变”(Mutiny),声称驻扎开罗的第3步兵团奉命开拔到亚历山大引发“兵变”。他哀叹,到1882年2月时埃及咨议会(Chamber of Notables)“完全处于叛变而成功的军队的影响之下”,“幸运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现在阻止埃及革命为时已晚……”“奥拉比不仅得到了奥斯曼帝国素丹的鼓励,而且这场民族主义事业的英国同情者的建议,往往巩固运动中军方和文官之间的联盟。”对于英国舰队1882年7月11日轰炸亚历山大、侵略埃及的野蛮行径,克罗默竟然认为是必要的“自卫手段”,“在奥斯曼帝国或国际社会没有采取有效行动的情况下,镇压阿拉伯人的责任就转移到了英国身上”。他还诡称“埃及人也普遍对英国的干预感到满意”。克罗默承认一些英国人把奥拉比视为民族英雄,但他自己的结论是:奥拉比作为赫底威的臣民,犯有叛国罪和叛乱罪,(即便)被军事法庭审判后处决,“不会有任何不公”。
《剑桥埃及史》在国际社会和中国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颇受追捧。1998年英文版第2卷第9章的标题是“奥拉比革命(Urabi revolution)与英国的占领(1879~1882年)”,似乎与埃及学术界的观点趋于一致,但其实不然。该书认为:“1881年9月至1882年9月间埃及的奥拉比革命,竭力削弱英、法的财政和政治控制、土耳其—契尔克斯人对高级军官职务的垄断和赫底威的权力,”而在埃及的赫底威陶菲克党人和许多西方人眼里,奥拉比运动无非是军队的反叛事件。这似乎从反叛论往前推进了一步,而且该书对奥拉比和赫底威陶菲克的社会支持力量进行了描述,但是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露出马脚:“迄今为止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相反,革命的失败反而加剧了这场革命竭力扭转的趋势,即埃及的殖民化。言下之意,这场所谓的革命是无用功,反而阻碍了埃及历史的进步。
那么,杨先生在《埃及近代史》一书中持何种立场、如何书写这场可歌可泣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呢?首先,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埃及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立场上,激情澎湃、浓墨重彩地讴歌埃及民族领袖和民族英雄艾哈迈德•奥拉比领导的伟大事业。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埃及人民的热爱和对埃及统治阶级、对殖民主义势力的痛恨。他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英国殖民势力的走狗、埃及首相努巴尔在1879年“二一八”事件中出的“洋相”:努巴尔骄横跋扈,从来不把埃及“乡巴佬军官”放在眼里,但是“军官和士兵上前揪住他的衣襟,把他从车上拽下来,摔倒在地,打了他一记耳光,给了他一拳。”英国殖民鹰犬、在埃及“欧洲内阁”中担任财政大臣的威尔逊见状,气急败坏,急忙上前搭救,挥舞手杖,殴打示威者。“示威者怒火中烧,揪着威尔逊的胡须,把他和努巴尔一起带到财政部,关在一间屋里,占领了财政部大楼……”杨先生不懂得、不屑于所谓的价值中立,爱憎分明,旗帜鲜明地为埃及人民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主义斗争摇旗呐喊。
其次,由表及里,抓住事件的本质,对奥拉比运动进行准确定性。杨先生对埃及学界的观点了然于胸:“埃及史学家通常把它称为‘奥拉比起义’或‘奥拉比革命’”,或“忠诚的人民革命”,“各阶层人民参加的民族革命”。先生反驳道:“事实上,它既非暴力革命,又非武装起义,而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因为这场运动所要求的只是对现存制度的某些改良,以求得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这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英法殖民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显示了以土著军人为后盾的初兴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潜在力量。他把这场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76~1879年2月),奥拉比作为土著军人的领袖极力反对赫底威在国内的民族压迫政策,以维护土著军人特别是土著军官的利益;第二阶段(1879年2月~1882年5月),奥拉比代表初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发起了埃及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第三阶段(1882年5月~1882年9月),奥拉比作为全民族的领袖领导埃及人民进行英勇的抗英战争。
再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阶级分析方法透视奥拉比运动背后的阶级和社会力量。不少西方学者惯用的话语陷阱之一,是就事论事地栽赃历史运动中的个人。比如,对于1907年在亚历山大建立新祖国党的终身党主席穆斯塔法•卡米勒,诬称他在官场上失意,所以建立政党、创办《旗帜报》,以泄私愤。对于奥拉比为首的土著军官,他们也是这样妖魔化的,声称他们只是为了个人的晋升和利益。杨先生岂能为浮云遮挡,受其蒙蔽,早就洞烛其奸。他深入研究19世纪后半期埃及城乡民族资产阶级的初步发展,从地主阶级的分化、土著知识分子的兴起、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在埃及的传播和意识形态斗争,以及英法殖民势力、奥斯曼帝国和埃及本土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剖析奥拉比运动,从而得出深刻而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的结论。
杨先生指出,既然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就必须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成立于1876年的青年埃及协会,是以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土著军官为主的秘密组织。埃及青年协会创办了《艾卜•纳札尔报》。这份报纸以广大埃及人民熟悉的埃及方言讽刺欧洲人在埃及享有的治外法权和赫底威伊斯梅尔的弊政,深受民众喜爱。1878年,部分议员为了反对“欧洲内阁”企图解散咨议会,秘密成立祖国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除少数知识分子外,大多是开明地主。青年埃及协会主要代表初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缺乏社会基础,因而在地主阶级中寻找有共同语言的人,于是1879年与祖国协会合并,改名为祖国党。11月4日,祖国党改组,奥拉比任党主席,但依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相当松散的政治联合体。祖国党提出了一个深得民心的口号:“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土著军人最初提出这个口号,用来反对土耳其—契尔克斯族军官,后来演变成为反对英法殖民主义、奥斯曼帝国和赫底威的强大武器。
他继续明确指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与封建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利益关联的开明地主在运动的关键时刻见风使舵甚至反戈一击,是奥拉比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祖国党的创始人之一谢里夫,是土耳其族法官之子,拥有数千费丹(1费丹约合6.3市亩)的土地,与王室关系密切。他狂妄自大,鄙视土著埃及人,认为“埃及人年幼无知,对他们要象对待儿童一样。我给了他们一部适合于他们的宪法,如果他们还不知足,就让他们在失去宪法保障的情况下去蛮干吧!我创建了祖国党。他们离开了我,将寸步难行。”
最后,杨先生如实书写埃及人民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评述运动领袖奥拉比的是非功过。奥拉比1841年出身于尼罗河三角洲小地主之家,父亲是村长,拥有8.5费丹土地。奥拉比幼年念私塾,8岁时进入爱资哈尔,学习语言和宗教,13岁入伍,开始戎马生涯。他深得当时的执政者赛义德赏识,6年内由无名小卒晋升为陆军中校。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口才极好,善于演说,具有打动民众心魂的领袖品质和巨大魅力。他认为,埃及“必须有一个根据宪法产生的代议制政府”,正是在奥拉比运动期间埃及出现了第一部具有宪法性的《基本法》。然而,奥拉比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他接受的教育有限,缺乏世界视野,对先进的欧洲所知甚少,夜郎自大。他曾经说:“我们比法国这个国家强大。”又说:“埃及的直接(力量)和军队,不单可以抵抗英国人(的侵略),而且可以(抵抗所有国家)三年的侵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打进埃及。”他认为英国人没有力量进行地面战争,“离开了大海,就会死去”。他发表声明,绝不屈服于欧洲或土耳其。他说:“让他们派遣欧洲或印度或土耳其的军队来(进攻我们)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捍卫我的祖国。唯有我们全都牺牲,他们才可能拥有我们的祖国,那时已是废墟一片了。”
奥拉比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军事筹谋和指挥能力有限。在战略上,他遭到英国人的欺骗,认为英军不会偷袭苏伊士运河,从东线直下开罗。亚历山大失守后,他在亚历山大东南面的道瓦尔村构筑第一道防线,在阿布基尔构筑第二道防线……74%的兵力部署在西线。而在东线,仅部署了26%的兵力,首都开罗门户洞开。狡猾的英国侵略军声东击西,佯攻道瓦尔村,主力直扑苏伊士运河。这一失误直接导致1882年9月14日,开罗沦陷。
沦落天涯,遭受流放之苦的奥拉比,晚年回到开罗,1911年在开罗默默无闻地去世,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有的学者把他称为“农民领袖”,把他的改良思想说成“首先代表农民的迫切要求”。对此,杨先生认为“不妥”,“缺乏分析”。的确,在奥拉比运动期间,埃及多个省份发生了农民夺地、抗租抗税的斗争,但这是遭受双重压榨的穷苦农民的分散、自发的行动,与“奥拉比革命”相伴而生,却并非“革命的产物”。恰恰相反,奥拉比本人也逐渐从受到压迫的土著军官,变成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分子。奥拉比晋升少将前,已经拥有超过200费丹土地。(1952年埃及实行第一次土改,规定地主占地的最高限额为200费丹,其子女可获得不超过100费丹的土地)晋升少将后,又低价购买数百费丹土地,到1882年被捕时拥有870.5费丹土地。关键在于,奥拉比和其他运动领袖脱胎于封建主义,与封建势力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是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是奥拉比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埃及近代史》这部著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近代埃及两对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为主线,以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生福祉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紧扣埃及的发展和现代化这个主题,建构出完备的埃及近代史学术体系,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爱憎分明,为劳动人民鼓与呼的话语体系,依然可以借鉴。这部作品如同陈年美酒,历久弥香,酒香何惧巷子深,值得细细玩味和用心品鉴。相反,当下的有些学术著述,或舍本逐末“洋八股”严重,或陷入资料泥沼而碎片化,或掉入西方话语陷阱却浑然不知自鸣得意,凡此种种,恕不一一列举。新出现的事物,未必是代表事物发展方向的新事物。重读过往经典,品鉴名人佳作,从中汲取有益养分,对于构建中东非洲史乃至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大有裨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非洲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毕健康供稿、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