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南强世界史系列讲座纪要|拱玉书:从最早的文字到最早的文学
2022-10-14

2022年9月39日厦门大学历史系“南强世界史系列讲座暨强基拔尖人才培养系列讲座”线上特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拱玉书教授以《从最早的文字到最早的文学》为题进行演讲。讲座伊始,拱玉书教授先对本次讲座的主要对象——楔形文字文明的时空范围加以介绍:公元前3200年,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语“两河之间”、亦即今天伊拉克南部诞生了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字体系,这一书于泥板的楔形文字文明传承数千载之久,历经早王朝、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巴比伦及亚述诸政权而兴盛不衰,波斯征服后虽逐渐衰落,但仍不绝如缕、直至公元后74年仍有泥板出土,此后方才“寿终正寝”。然而,回到文字诞生之初,彼时虽有词汇,但无篇章,文字之用,大抵记录账目、罗列名单;及至文学滥觞,楔文书写系统才真正臻于完善。由此,本次讲座便正式围绕两大主题——“最早的文字”与“最早的文学”加以展开:前者介绍楔文发展源流、古人文字起源传说、今人文字起源理论以及楔文同汉字的共通之处——基于“许慎六书”加以类比;后者则介绍不同时期的代表文学作品,并以苏美尔语、阿卡德语的各自吉尔伽美什史诗系列为例进行个案分析,帮助听众一窥两河文学之堂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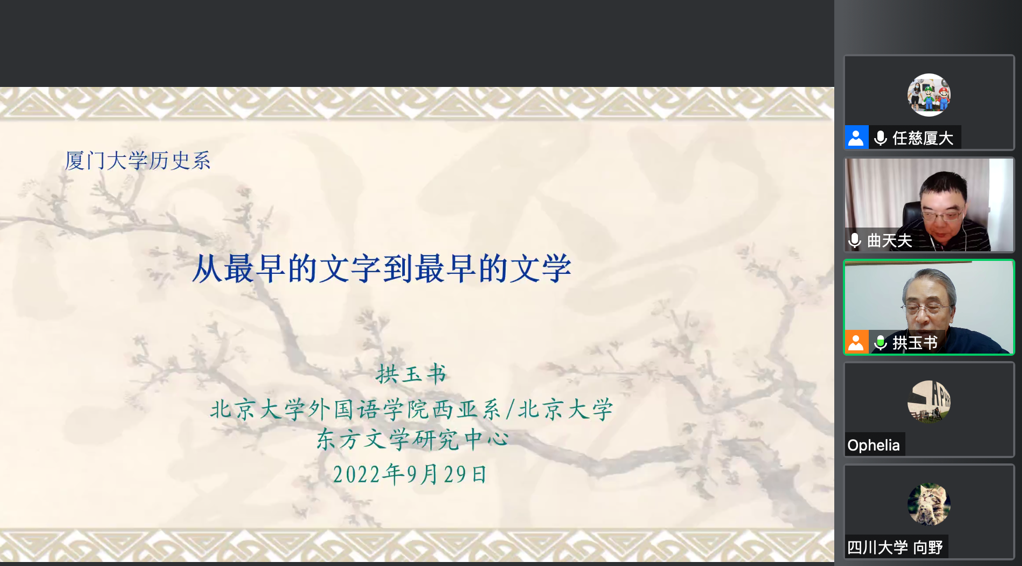
第一部分:最早的文字
目前已知最早的楔形文字文献出土于乌鲁克文化第四期(Uruk IV, ca. 3350 - 3200 BCE.),以经济文献为主。需要特别说明,当这一最早的文字体系为考古学家发现之时,似乎就已经相当成熟。为满足当时以神庙为中心日常管理活动的需要,文字应运而生,巨量的泥板用于记录谷物、酒酿等各色收支名物及其数量,而神庙事实上也就构成了早期国家的统治中心。乌鲁克文化晚期共出土6000余块泥板,这其中经济文献占据85%的绝对多数;剩余的15%则代表了早期文字的第二类用途——用于编纂辞书。所谓辞书(Lexical Texts),或称表类文献,乃是对专有名词所进行的罗列,代表作品是公元前2600年的《人表》(ED Lu A),记录了当时各类职业,如祭司、书吏、工匠、牧人,反映出社会阶层的分化。除此之外,草木、金石、鸟兽、器皿、城邦、神祇皆可成为列表的题材。对各类事物分门别类、汇编列表,一方面或许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教学方式,另一方面或许代表了人类历史上初阶的学术探索。
鉴于早期文字自发现之时便已颇为繁复,此前从无到有的过程即便借助考古手段依然混沌不明,故而需要通过一些合理假说来构拟出文字起源的可能进程。在介绍今人假说之前,苏美尔人自己的文字起源认知也不容忽视。依据《恩美卡尔与阿拉塔之王》(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的传说,乌鲁克之王恩美卡尔派遣使者翻越七座大山、前往阿拉塔城向当地统治者索要金银矿产作为贡赋,后者不愿轻易臣服、引发局势升级,使者带去的外交辞令愈发冗长、导致无法一一复述,恩美卡尔遂将话语写于黏土、交与使者,文字也因此发明。上述传说固然不可尽信,但古人所认为的文字是由智者一举发明、而非经历漫长的时间逐渐演化而来的观点也不无道理。毕竟,文字从无到有的演进太过迅速,短时间内仿佛经历了重大突变,加之作为符号系统的文字设计统一,说文字是被人“发明”的也并非不可。当然,此处的发明者大概率不止一位。而一旦由某一群体最先尝试,文字从产生到广泛应用前后可能不过数代人的时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从考古学层面上很难捕捉到早期文字演化的蛛丝马迹。
不过上述说法仅仅只是一种猜测。目前学界相对认可的说法是“陶筹起源说”;具体的讨论可以参看丹尼斯·施曼特-贝瑟拉(Denise Schmandt-Besserat)《文字起源》一书(已有中译)。所谓“陶筹”(token),乃是用黏土抟成事物的大概轮廓、再经过烧结而成,在经济活动中,易于携带的陶筹象征了所涉物品,便于管理人员清点收支数目。公元前4000年以降,陶筹的外形愈发丰富,发展出容器、动物、几何等多种形态。陶筹体积小巧,实际应用中往往塞入空心泥球当中、以防遗失。再到后来,使用者便将陶筹按压在封泥表面、形成印文,与内部陶筹互证;逐渐地,二维的印文取代了三维的陶筹本身,开始向更为抽象的文字形态过渡,印文封泥也转化为平面的楔文泥板。陶筹起源说的合理之处在于,不少陶筹印文能够与之后的楔形文字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例如,扇形纹样象征牛首,日后楔形字符AB2(母牛)由此而来;圆形内嵌十字象征绵羊,日后楔形字符UDU由此而来。纵使如此,陶筹起源说也只能解释一部分楔形文字的由来。典型地,楔形文字系统并不是完全由象形符号构成,许多字符实际上是用于表音的;这些表音符号从何而来,陶筹起源说并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尚待之后的学者提出不一样的见解。
文字诞生之初,虽然偏重象形,但同汉字一样,为适应复杂的书写需求,楔文造字法并非象形一种。依照东汉许慎“六书”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略加改造,今天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楔文六书”:一曰象形。如前所述,自然事物多为象形,另外苏美尔动词如“走”(DU)也可以从类似“足”的形状演化而来。二曰指示。SAĜ本为“头”之义,头字用小斜杠(gunû)标记下半部分,变得到KA(即“口”字)。三曰会意。两字组合、意义叠加获得新字,“口”加“水”(A)得到“饮”(NAĜ),“目”(IGI)加“水”得到“泪”(ER2)。四曰形声。“蹄”(ĜIR3)字下书声旁“A”与“LIM”得到“ALIM”,意为“野牛”;方框(ĜA2)象形,内书“ME”、“EN”二字,即为“冠冕”(MEN)。五曰转注,许慎所谓“同意相受”。IDIGNA本为水鸟,用以指代底格里斯河;INANA本为芦苇,用以指代女神伊南娜。六曰假借。“箭”与“命”在苏美尔语中发音相同(TI),便借前者的符号书写后者。理论上,象形在前,后面五类造字之法皆由象形派生。直接套用许慎的理论固然有削足适履之嫌,但不同文明当中,扩大书写词汇量的基本方式应当有相通之处,也可适当借鉴。

第二部分:最早的文学
现阶段讨论早期两河文学的难点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其一,尽管早期文献主要用苏美尔语书写,但是两河流域实际所使用的语言绝对不止苏美尔语一种,尤其是在阿卡德王国时期,我们观察到了长期被压抑的阿卡德语传统异军突起,并留下了大量的王室铭文,这使得我们无法确定此前是否有着同苏美尔语一样悠久的阿卡德口头文学传统。其二,尽管两河的神话传说源远流长,今天学者所能获取的抄本却产生偏晚,基本不早于古巴比伦时期、并且不书创作者名字,这就导致了文学作品的断代尚不明确,换言之,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作品起初于何时、由何人所作。考虑到上述问题的复杂性,本场讲座对相关讨论进行了简化处理:首先,将“文学”一词限定为狭义的神话、史诗等纯文学作品,遂将王铭排除在外。如此一来,以王铭为代表的早期阿卡德语文学创作传统就暂时不在考虑的范畴;另外依照现存抄本,阿卡德语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品应当是古巴比伦时期诞生的《阿特拉哈西斯》神话,时间上晚于苏美尔语文学,此次讲座略去不谈。换言之,“最早的文学”仅指苏美尔文学。其次,本次讲座对苏美尔文学的“创作阶段”与“传抄阶段”依照政权更迭的脉络进行明确划分。具体来说,除少部分特例(如早王朝时期的《舒鲁帕克教谕》)之外,目前已知绝大多数用苏美尔语所书写的文学作品应当创作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ca. 2100 - 2000 BCE.)、即苏美尔文学的鼎盛时期,并且传抄、整理于王朝覆灭之后的古巴比伦时期(– ca. 1600 BCE.)。
接下来,讲座按时间线索对苏美尔文学作品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梳理。早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只有零星出土,发现于尼普尔西北部(Abū Ṣalābīkh)的《舒鲁帕克教谕》(The Instructions of Shuruppak)是其中的代表。这篇所谓的“文学”本质上是道德训诫,以父亲的口吻教导儿子不宜行窃、不宜斗殴、不宜吹嘘、而应早日结婚置产。阿卡德王国时期,上层的统治者虽然使用阿卡德语,但为维系所辖苏美尔民众,仍鼓励苏美尔文学的创作。开国之君萨尔贡将自己的女儿恩黑度安娜(En-ḫe2-du7-an-na)任命为乌尔城女祭司,后者留下伊南娜颂歌四首,诗中有“吾乃恩黑度安娜”之语,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诗人。
尽管上述作品已开苏美尔文学之先河,但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内容来看局限仍特别明显。乌尔第三王朝真正标志着苏美尔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只可惜,不同于恩黑度安娜的特例,作品背后的创作者名字早已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以围绕吉尔伽美什的史诗故事为例,这一时期就有《吉尔伽美什与阿伽》、《吉尔伽美什与洪巴巴》、《吉尔伽美什与天牛》、《吉尔伽美什与冥府》、《吉尔伽美什之死》等系列作品五篇(先后顺序并不确定)。《阿伽》的故事主要讲述基什王围困乌鲁克,吉尔伽美什先后召开长老大会与少壮大会商议对策,前者畏战、后者则誓死效忠。在出城的使者被阿伽扣押之后,吉尔伽美什本人亲临城楼、指挥作战,其野牛般的怒目、青金石似的胡须一如使者之所言。阿伽望其神武若此、心生畏惧,遂遭生擒,但吉尔伽美什又仁慈地将他赦免。《洪巴巴》故事中的洪巴巴本是山中雪松林的守护神,但吉尔伽美什为砍伐雪松,谎称欲将自己的姐妹许配与洪巴巴作为妻妾、同时不怀好意地报上死敌的名字(包括阿伽的父亲),接着又献上各色佳肴、珍宝,大肆吹捧,七番天花乱坠的描述诱骗得洪巴巴一一褪去身上的七重宝光(me-lem4)、并以宝光作为交换,结果却导致自身法力全失、遂被活捉,但最终洪巴巴的泪水还是让吉尔伽美什决定兑现自己的承诺。《天牛》故事残缺严重,女神伊南娜因不明原因想要用天界的公牛杀死吉尔伽美什,天牛在下界吃光草场、喝干河水,而彼时吉尔伽美什正令乐师奏乐,在得知消息后依然斟酒不误。饮毕,遂同恩启都一道斩杀天牛,牛肉分与市民,牛角制成杯盏为伊南娜献祭。《冥府》故事的开篇则颇为迂曲,一日,漫步幼发拉底河边的女神伊南娜拾得大水冲走的上古神树一株、植于园囿。原计划待树木成材、制成家具,不料怪鸟栖于树顶,大蛇盘踞树根,幽灵依附树干,女神遂找来吉尔伽美什搬出巨斧、赶走精怪,木材制成的宝座交与女神,制成的“球”(ellag)与棍则作为后者的报酬。只可惜击球游戏中发生了死亡事故,家属的恸哭引得幽冥在夜晚收走了球与棍。吉尔伽美什忠实的仆人恩启都欲为主人取回球、棍,自告奋勇地前往冥府。吉尔伽美什交待冥府事宜,再三告诫绝对不能亲吻认识的死者,恩启都未能听取忠告,一去不回。所幸吉尔伽美什为好友的祈祷打动了天父恩利尔,后者派太阳神开出通路、让恩启都的“魂魄”(si-si-ig)得以与吉尔伽美什相见。《吉尔伽美什之死》则是英雄的挽歌,追忆其生前功绩,另外提及了吉尔伽美什杀死洪巴巴,拜谒大洪水前的孑遗、永生的齐乌苏德拉(Zi-ud-su3-ra2)的事迹,同时还暗示了吉尔伽美什在死后与恩启都的重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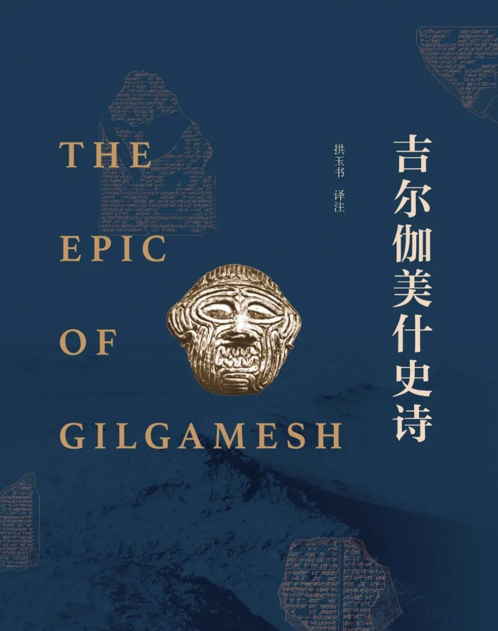
讲座的最后,为了让听众对于两河文学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拱玉书教授介绍了古代标准版的吉尔伽美什系列作品。尽管这个由中巴比伦书吏(Sîn-lēqi-unninni)用阿卡德语书写的作品,从时间上(ca. 1300-1200 BCE.)看已经算不上是“最早的文学”,但是这一共计十二泥板的长篇与上面提及的苏美尔系列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阿伽》中二级会议的决策模式被照搬至后来的史诗;斩杀洪巴巴与天牛的情节对应标准版第三至六块泥板;吉尔伽美什的挽歌被挪用过来哀悼死去的恩启都;齐乌苏德拉,阿卡德语乌塔纳皮什提(ūta-napišti),则在第十一泥板中向吉尔伽美什讲述了大洪水的具体经过;至于《冥府》故事,则对应标准版的最后一块泥板,基本上译自苏美尔版本,用以作结。
(撰稿整理|雷智淋、李洹;审阅|曲天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