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怀念邱汉生先生
2022-11-18

上世纪80年代社科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部分学者在外老家中前排左起:何兆武、侯外庐、邱汉生、孙开泰后排左起:黄宣民、唐宇元、步近智、卢钟锋、姜广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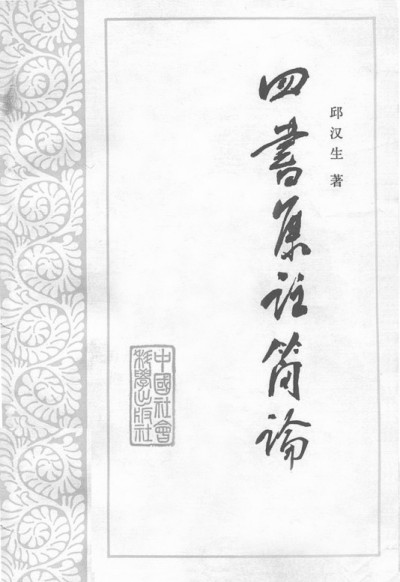
《四书集注简论》书影,封面题签为侯外庐先生
6月18日,是邱汉生先生的忌日。悠忽之间,30年过去,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先生的循循教诲,仍谆谆在耳。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迎来了春天,侯外庐先生门下的学者重整旧业,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和研究成果,邱先生撰著的《四书集注简论》1980年在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辑校的王安石《诗义钩沉》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而更重要的,是他受外庐先生委托,组织侯门学者开始了《宋明理学史》的筹备和撰写工作,张岂之先生也加入了组织领导,他要求我将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定在17世纪的明末清初。
1981年秋天,邱先生邀请我参加“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当时外老的研究生崔大华、柯兆利、姜广辉也参加了。会议期间,我陪邱先生拜访了美国著名汉学家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1919-2017),他比邱先生小7岁,看起来很健康。邱先生与他讨论了黄宗羲和《明儒学案》等问题。那次会议国内外学者云集,冯友兰先生与贺麟先生都参加了。会议期间在杭州楼外楼吃饭,我还给几位先生拍了照片,后来发表在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世界汉学》上(我当时任副主编)。
会议期间,主办方组织参观富春江,停车步行时,路不好走,我一直陪在邱先生身边,那天恰好薄云绕山,轻雾漫江,气象恢弘。他一边走,一边吟诵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并且告诉我,这是当年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称颂严子陵的话,给我讲了严子陵垂钓富春江的故事。结合当时场景,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在以后与邱先生的交往中,我深深感到,这几句诵咏不就是先生风范的写照吗? 后来我才了解到,邱先生自幼喜诗文,9岁参加家乡三阳镇地区各小学国文会考,两次名列第一。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期间,就撰写了《中国文学史略》一书,古典文学功力了得。
80年代初,邱先生几次来西安,我陪他到陕西师大讲课,他请我“写黑板”。就是他说到关键词,我就在黑板上写出来,当时还真有点紧张,生怕写错。邱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在上海,蔡尚思先生很器重他,推荐他在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教授中国通史。他也帮助蔡先生抄写整理过大量历史资料。邱先生讲课,声音洪亮,逻辑清晰,记录即成文章。这得力于他年轻时在上海、海门、新昌、南通等地中学教书生涯和深厚的文学功底。
80年代邱先生在西大、师大讲学,内容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朱熹与《四书集注》。因为这时他刚刚出版了《四书集注简论》。他对于朱熹的研究,可谓细致入微、表里俱到。但是这部书的主干,是在70年代写成,因此受时代的影响,有些看法在书中还不能大胆直陈。
2018年,我受朱子学会之邀,到福建南平参加“纪念朱子诞辰888周年”学术研讨会,我的与会论文中,涉及到邱汉生先生对《四书集注》的研究,其中下列要点是我学习《四书集注简论》而得出的体会:
1攉朱子对“天理”的追求,表现了封建时代思想家对宇宙正义信念的孜孜追求。这一点在今天仍具有超越的意义。
2攉朱子用一生心血对先秦以来儒家经学文献的归纳梳理,其成果就是《四书集注》,这对弘扬南宋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3攉朱子继承孔子,不论在讲学,还是著述方面,都成为古代教育家的典范,这告诉我们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现象: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是用思想服务于社会的伟大教育家。
4攉朱子的献身精神和伟大人格力量,具有中国哲学的特色,是超越时空限制的中国思想史的宝贵财富。
上述浅论在今天看来还有待深入,这里只是一个历史记录而已。在《四书集注》的“后记”中,邱先生说:“论述宋明理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分析宋明理学的积极的一面,也俟诸异日。”这句话,在后来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这部大著作中,得到了实现。
记得是1986年,我从西安来京给邱先生呈送岂之先生统稿的《宋明理学史》,邱先生收到稿子后十分高兴,那天中午请我在他家吃的饭。后来他在给黄宣民老师的信中写道:
“理学史下卷,稿经岂之审阅修订,大体就绪。三月初,他派任大援同志送稿来京。我和钟锋检查后,即交出版社。作为第一季度发稿,年内可以出书。我们此卷,外老能看到样书,就算工作有了成果。……”
回想起40年前一幕幕的往事,令人不能自已。我不禁又想起邱先生给我讲过朱熹对“圣贤气象”的讨论。他说,朱熹的这种表述方法,是用形象的文笔,比况人的胸襟、志趣、器量、态度、德业等等,“颇可注意”。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我时常想,邱先生是一种什么气象呢? 借用理学家朱公掞对程颢的评价,大概是“如沐春风”吧。但这种春风,是二月的春风,带有一丝坚毅料峭。给人和煦温暖而又使人自励警醒。
前不久读《邱汉生诗集》,其中有一联写道:“瘦骨尚堪千历劫,我心清似水晶盘。”我心有所动,将后一句用作纪念岂之师在西北大学执教70年文章题目。我以为,侯门在“文革”结束之后,经过邱汉生先生、张岂之先生,有一个发展的兴盛阶段,值得总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气象,就像量子缠绕,形成一种既神秘、又伟大的力量。我心底不觉生出颜渊的喟然之叹: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作者:任大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