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滢雪:日本学者的奥斯曼帝国史新解
2020-12-21
(首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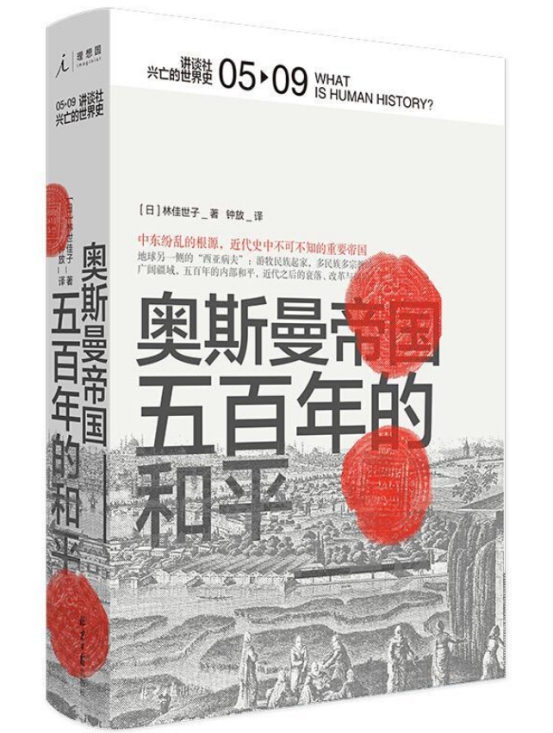
2018年是奥斯曼帝国解体100周年,奥斯曼帝国历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近期,西方学者有关奥斯曼帝国史著作已有数十部被介绍和翻译到国内。如果说,欧洲学者研究奥斯曼帝国是因为这个帝国的领土包括东欧,并与欧洲大国多次进行较量,使得欧洲史和奥斯曼帝国史无法截然分开,那么,远在亚洲东部的日本,有学者研究奥斯曼帝国,只能是出于兴趣或者是了解世界历史整体的需要。就像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一样,研究奥斯曼帝国完全是探究“外国史”,少了一份历史亲近感,却多了一份由距离带来的客观性和宏观视野。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林佳世子著《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钟放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让学界有机会了解日本学者对奥斯曼帝国史研究的状况。林佳世子现为东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综合国际学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为西亚社会史、奥斯曼王朝史。代表作有《奥斯曼帝国的时代》,编著有《记录和表象——史料中的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研究指南》、《伊斯兰书籍的历史》等。
《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研究从14世纪初到19世纪初的五百年间,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逐步崛起、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全书分为八章:安纳托利亚时代(1050-1350)、在巴尔干扩张(1350-1450)、在苏丹麾下战斗(1450-1520)、苏莱曼一世的时代(1520-1560)、奥斯曼官僚的时代(1560-1680)、近代奥斯曼社会、繁荣中的不安(1680-1770)、奥斯曼体制的终结(1770-1830)。
奥斯曼帝国研究的新视角
按照林佳世子的理解,五百多年前一个伟大的帝国崛起于西亚北非,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世界历史。如果把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作为奥斯曼帝国的起点,到1918年解体,帝国经历了将近五百年的时间。在这五百年里,奥斯曼帝国继承了安纳托利亚、巴尔干和阿拉伯等地区的既存文化传统,吸纳了各种制度,有效地统治着上述区域。在最辉煌的日子里,奥斯曼帝国的事业就是对外征服。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帝国维持着内部的安定,并实现了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和平。林佳世子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几个不同的视角。
(一)“非土耳其”的研究视角
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末走向终结,经过持久的抗争,境内各民族国家走向独立,最后剩下的部分就是“土耳其人的国家”。从这段历史来看,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自然被视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那些独立的民族无法理性地面对帝国的统治时期,把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视为帝国的负面遗产,否认自己的“奥斯曼帝国后裔”身份,从而导致一些学者将奥斯曼帝国看做是土耳其人统治的国家,过多地强调了帝国的土耳其属性。
林佳世子在探究奥斯曼帝国五百年历史的时候,更多地采用了“非土耳其”的研究视角。作者首先讨论了土耳其人在帝国中的地位:(1)帝国常备军耶尼切里军团中几乎没有土耳其人;(2)伊斯坦布尔那些华丽清真寺的设计者不是土耳其人;(3)“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是指农民和牧民;(4)土耳其的游牧民族经常发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等等。由此可见,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并不突出。
其次,关于帝国的发源地。作者认为,奥斯曼帝国不是土耳其人以安纳托利亚为据点建立起来的国家,巴尔干地区才是帝国的发源地。林佳世子认为,帝国在占领巴尔干等边缘地区后,按照“掠夺—同盟—臣属—直接统治”的顺序,分阶段加深统治。奥斯曼帝国是以巴尔干半岛大国的身份成长起来的,后来才征服了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国家,帝国也不是土耳其人统治的国家,只是在帝国灭亡之后,其历史才开始“土耳其化”。
(二)“非伊斯兰帝国”的研究视角
奥斯曼人在建国初期就从边疆地区接受了伊斯兰教。在此后五百多年里,帝国一直将伊斯兰教视为国教,伊斯兰也成为大部分奥斯曼人集体意识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学者倾向于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伊斯兰帝国”。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中写道:“奥斯曼帝国由奠定直到灭亡,始终是一个致力于促进或保卫伊斯兰教权力和信仰的国家。”那么,奥斯曼帝国是否算得上是“伊斯兰帝国”呢?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林佳世子首先对伊斯兰帝国下了定义:那些尽力扩大伊斯兰教,国家的运行与社会生活体现伊斯兰教理念的国家才能被称为“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确实高举伊斯兰教旗帜,在伊斯兰教名义下与基督教欧洲进行“圣战”,还利用伊斯兰教法治理国家。但是,我们要看到统治者实行这些措施的实质:(1)在伊斯兰教的名义下宣传包含正义和公平在内的普遍理念,有利于统治的稳定;(2)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精神武器,能够鼓舞士气,有利于帝国在战争中取胜;(3)伊斯兰教法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有利于统治境内的非伊斯兰教徒。所以,统治者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推行各种措施,目的并不是为了扩大伊斯兰教,而是为了更好地统治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奥斯曼帝国不能与伊斯兰帝国划上等号。不应过多的强调帝国与宗教的关系,否则对很多历史事实都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三)“比较研究”的视角
昝涛副教授曾说过,近年来日本学界在研究奥斯曼帝国近代史时,引入了与日本进行比较的视角。奥斯曼帝国在1699年签订《卡洛维兹条约》,此后开始走下坡路,帝国昔日荣光不再,被西方人称作“欧洲病夫”。大约在奥斯曼帝国走向衰亡的同一时期,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诸国的发展机制也面临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奥斯曼帝国与日本进行对比研究有其意义。到了近代社会,奥斯曼帝国的政府机构和宫廷分开,宫廷内的阴险权谋和血腥政变已经成为历史演进的插曲。日本的德川幕府也是如此,幕府内部中央集权制走向瓦解,各派势力你争我斗,不得安宁,这是相似的方面。
林佳世子在书中也对晚期奥斯曼帝国与明治维新下的日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她指出,当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维持统治秩序,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后的帝国成为“对等的参加外交活动与国际战争,在绝对王权之下依法行政,以缔造‘国民’为目标的近代官僚制国家”。而比奥斯曼帝国晚五十年进行近现代化改革的日本,也抱有同样的理念。奥斯曼帝国在彻底崩溃前,不时地应时代的要求寻找最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一时期和日本从明治维新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大致相同,总计约八十年。
关于帝国疆界与伊斯兰正当性
林佳世子与其他奥斯曼帝国史研究者一样叙述了帝国从崛起到衰落的过程。不过,这位日本学者特别强调了衰落过程中的两方面:
(一)帝国在国际关系中无法维持领土界限
奥斯曼人的祖先是中亚突厥人的一支,游牧民的特性要求统治者不断扩张领土,获得战利品,进而维持国家的繁荣与和平。帝国的前十位苏丹积极进取,不断扩大领土,使得帝国最盛时边界达到了今天的欧洲东南部、亚洲西部以及非洲北部。但是,自苏莱曼大帝之后,帝国的苏丹大多为平庸之辈,对征服失去了兴趣,对外政策开始走向守势。帝国在东边无法进入波斯,在印度洋被葡萄牙人驱逐,在克里米亚及外围地区受到俄国人阻挠,在非洲无法扩张,就连地中海也落入欧洲人之手。
奥斯曼帝国拥有如此广阔的领土,但是作为核心的直接统治区域只有安纳托利亚、巴尔干、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剩下的边缘地区由政治上独立运作的省和属国组成。在这些边缘地区,帝国通过任命地区行政长官实行间接统治,将其作为直辖区域的屏障,避免战争带来的外部干扰。实际上,奥斯曼帝国从来就没有在这些地区进行过实质性的统治。18世纪之后,帝国在边缘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弱化。这一时期帝国全境的地方势力都在崛起,边缘地区的省和属国也发生了剧烈变动,开始摆脱其作为屏障的身份。除此之外,外国势力也积极干涉这些地区的事务,强化了这些地区的独立性。
在俄国的影响下,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在1828-1829年获得自治权,成为俄国的保护国;克里米亚汗国在1771年被俄国占领,随后被俄国吞并;18世纪30年代开始,埃及耶尼切里军团中的卡斯达尔派崛起,埃及的实权逐渐被军人实力派掌握;在伊拉克南部,帝国被迫承认哈桑后继者马木鲁克军政官的地位;北非的耶尼切里军团也逐渐本土化和门阀化,仅与帝国维持名义上的主从关系;阿拉伯半岛中部的瓦哈比派展开纯化伊斯兰的运动,沙特家族崛起,也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发起了挑战。在帝国的边缘地区,统治已经动摇。从来没有接受过帝国实质性统治的区域,独立性加剧,帝国政府通过任命地区的行政首长达到间接统治的方式已经难以奏效。由于在国际关系中无法维持领土的界限,帝国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二)基于伊斯兰教的统治正当性发生动摇
奥斯曼人最初在边疆地带接触到伊斯兰教,他们的信仰受到托钵僧、苦行者和神秘主义者的影响,具有尚武和朴素的宗教特点。在伊斯兰教的号召下,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欧洲进行了数百年的战争,将帝国边界不断地向西移动。帝国的统治者一直把自己视为伊斯兰教义和政治原则的实践者,把伊斯兰教作为公私生活的基础。伊斯兰教法成为国家的有效法律,国家给予执行这项法律的法庭和司法人员以充分的承认和充分的权力。此外,统治者实行宗教容忍政策,帝国境内的非伊斯兰教徒,可以根据伊斯兰法,保留自己的信仰、教会和相应的法规。
在这种统治框架下,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愿意承认苏丹的统治权,遵守伊斯兰教法,对帝国保持忠诚。但是,这种统治框架被接受的前提是“臣民得到安全保障且伊斯兰教徒和非伊斯兰教徒在经济上没有太大差距”。在最开始,帝国统治下的非穆斯林面临实际问题时,可以通过伊斯兰教法维持自己的正当权利,从而获得安全保障。而且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中都有穷人和富人,大家都是奥斯曼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成果的享受者,宗教信仰的不同并不影响社会地位。
但是,帝国后期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7世纪之后罗马天主教在帝国的传教活动不断扩大,帝国境内的天主教徒开始增多,威胁到了希腊正教会的统治。为了应对这种危机,希腊正教会开始推行新的组织化分级管理,对辖区内的教徒加强管辖。教会的希腊化引起了巴尔干等地教徒的不满,反希腊正教会运动在18世纪后半期迅速发展。帝国为了唤起希腊正教徒和亚美尼亚教徒对帝国的认同,对两地的教会进行关照。结果对“希腊人”的关照反而让属于其他“民族”的希腊正教徒感觉安全受到了威胁,动摇了这些教徒对帝国的忠诚度。
18世纪后,非穆斯林商人的经济实力增强,也加剧了他们和穆斯林之间的对立。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这三个民族善于经商,在帝国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民族在政治上处于不平等地位,造成民族对立甚至冲突。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徒和非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差别更加明显,从而导致非伊斯兰教徒对帝国的归属意识逐渐淡薄,并由宗教差别转为民族意识的差异。19世纪以后帝国治下的少数民族掀起了一系列民族运动,帝国基于伊斯兰教的统治根基受到严重动摇。
关于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
奥斯曼帝国是如何从兴盛走向衰落的,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中,把帝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机构的变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衰落以及精神、文化和思想的变化。杰森·古德温在《奥斯曼帝国闲史》一书中认为,奥斯曼的古老体制被破除之后,无法建立一个能取代并被所有政权都接受的新体制,由此导致了帝国的分崩离析。王三义在《奥斯曼帝国史六论》一书中,从帝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外债问题、边患问题、对外关系、西化和瓦解后的遗留问题等方面讨论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过程。
在林佳世子的这部著作中,作者也讨论了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原因。作者把帝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中央集权制度的瓦解。
奥斯曼国家在从埃米尔国发展到帝国的过程中,中央集权制不断发展,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统治国家的原则。在税收方面,帝国实行蒂玛制度。政府授予骑士农村地区的征税权,作为回报,骑士承担相应的军事义务。帝国通过这种制度,将当地的中间支配层大量吸收进来,逐渐稳定了统治。在军事方面,建立了以耶尼切里军团为核心的常备军。耶尼切里军团主要通过德米舍迈制度(征募基督教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来补充。他们有固定的军饷,只接受苏丹的统治,战斗力极强。在法律方面,明确伊斯兰教法和苏丹法之间的关系,确定伊斯兰教在帝国体制中的位置。谢赫伊斯兰地位提高,成为乌勒玛的最高职位。帝国乌勒玛分为麦德莱赛教授职位和地方法官两个系统,还规定乌勒玛的任用和晋升制度。在官僚体系方面,以大宰相为首的职业官僚集团形成。苏丹任命军人政治家组成行政官僚体系,官员之间职权明确,且存在着清晰的阶层结构。
但是到了18世纪后半期,统治帝国的各项制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帝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税收方面,帝国的主要征税体制由蒂玛制向包税制过渡。包税制是没收之前的蒂玛土地,将税收以县为单位汇总,然后由特定的征税承包人购买一段时间的税收制度。包税制的兴起造成了西帕希(封建骑兵)的衰落,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到了18世纪后期,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购买包税权,他们在征税过程中向农民借贷、开垦新农地、种植经济作物、集中土地,提高了自身的力量。他们都拥有私人武装,形成地方割据势力,这个时代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呈现出分裂的迹象。
在军事方面,耶尼切里军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耶尼切里都是军人子弟,军队开始世袭化。其次,越来越多的人混进了军队,包括农民在内的非正规军,导致军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耶尼切里军在和平时期的生活方式也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军人离开军营住在都市里,他们开始从事各种副业,扎根于社会基层,已经很难与行会区分。耶尼切里军既保持着原有的特殊地位,又进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这也成为政府长期无法推进有效的军队改革的根本原因。
在法律方面,法律规定的帝国的形态和真实的奥斯曼国家或社会的状况并不符合。根据伊斯兰的法律,统治者对其他宗教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但是,其他宗教的臣民被限制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严格地与穆斯林隔离开来,对帝国文明做出的贡献不大。除此之外,高级乌勒玛开始通过权力寻租确保自己的收入,地方法官的大部分业务也由代理官员执行,就连麦德莱赛教授的职位也可以成为买卖和租借的对象。这些导致司法人员的业务能力进一步下降。
在官僚体系方面,官员自身素质急剧下降。18世纪以后的奥斯曼帝国是多名实力派军人政治家对抗的舞台。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社会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以自己家族和接受薪俸的文武家臣为核心。政治家们向各级政府输送自己利益集团的人员,这种官场文化导致整个社会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官员接受政府任命以后越来越多地寻求代理人去做实际工作。官员们出卖官职的一部分,将政府支付的代替薪俸的包税权卖给第三方,导致帝国的官员群体日益庞大,但有名无实,。
早期的奥斯曼帝国被马基雅维利描述成一个“难以征服但是容易控制的帝国”。后来的事实证明,帝国的衰落,是大权从苏丹手里滑落到他的奴仆手中,是从内部开始并完成的。18世纪后半期,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变质,官职的权益化和地方势力崛起导致帝国已经无法对全境实施有效的统治,帝国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结。通过林佳世子《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一书,我们可以宏观把握这五百年历史的脉络,了解其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和长远影响。
(邓滢雪,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