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所邀请刘津瑜教授做学术讲座
2023-0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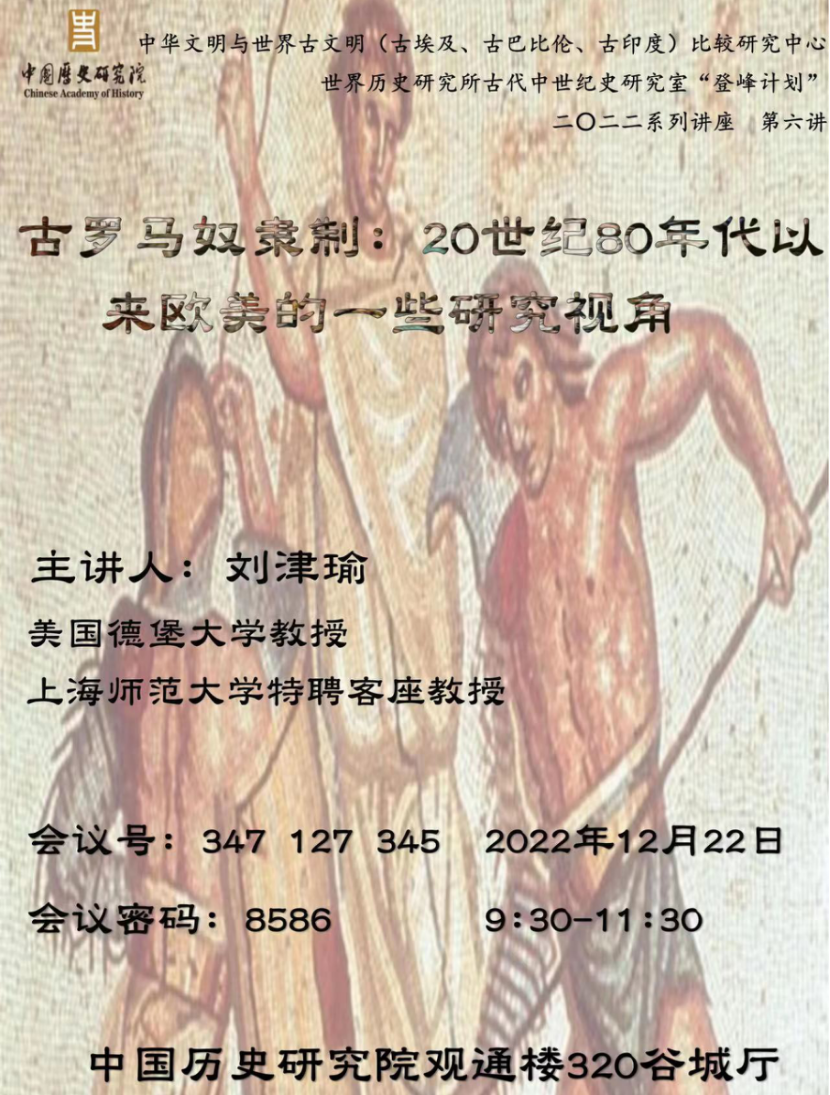
2022年12月22日,应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美国德堡大学古典系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津瑜在线上做题为“古罗马奴隶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一些研究视角”的学术讲座,对近40年来的欧美相关研究做了梳理。
刘津瑜教授从特尔图良笔下的一桩自由民儿童被贩卖为奴的故事谈起(《致万民书》Ad nationes 1.16.13–19),分析故事中蕴含的古罗马奴隶制元素和一些词汇的特定含义,进而介绍欧美史学界关于奴隶制研究的词汇和表述方面的新变化。
目前英文学术出版界和教育界在积极地推行新的表述方式,特别是不再将“奴隶主”和“奴隶”称为master-slave,而是称为enslaver-enslaved。这是因为slave一词容易使“奴隶”看起来是某种具有奴性的族群,而master一词体现了奴隶制关系中奴隶主的视角。新的表达方式通过主动态和被动态准确体现了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诸如“逃奴”(runaway slave)等奴隶主视角的表述也改为“奴隶制逃亡者”(fugitives from slavery)或“自我解放者”(self-emancipated, self-liberated)。古代世界的奴隶制被认为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2022年出版的一部史料集《希腊罗马奴隶制》(Greek and Roman Slaveries)的书名反映了这种认识。
近年来,一些熟悉的基本概念也得到了重新探讨。“戴镣铐的奴隶”(servus vinctus)以前通常被认为是奴隶戴着镣铐劳动,2011年乌尔丽克·罗特(Ulrike Roth)令人信服地论证戴镣铐是重罚奴隶的一种方式,并非指奴隶们都带着镣铐在田间干活。这些奴隶在被出售时,需要标明是否曾受过这样的惩罚。在帝国时期,奴隶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如果受过惩罚的奴隶得到解放,获得自由身份,是不能成为公民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这种说法。这通常被视为奴隶不被当作人看待的证据,但这个表述需要放在语境中来考量,而且instrumentum这个词简单地理解为“工具”也未必恰当。对照语句的出处——瓦罗《论农业》1.17.1-3的上下文,瓦罗在此讨论的是耕种土地所需要的配置,他指出有些人认为这分成两部分,即人(homines)以及协助人的东西,而这里的“人”是既包括奴隶也包括自由民的;另外一些人则把这些配置分成三部分,即“会说话的”(vocale)、“半会说话的”(semivocale)以及“无声的”(mutum)。“会说话的”这一类,所举的例子是奴隶;而“半会说话”的例子是牛;“无声的”这一类的例子是运货的车。也就是说,“奴隶”和“牛”、“车”一样都是例子而并不代表这些配置的全部。瓦罗在这一节中还特别强调所有的田地都是由人来耕种的:由奴隶或自由人或两者共同耕种。瓦罗提到大部分穷人及其家庭一起劳作,重活由雇工来作,比如收葡萄、打干草之类。瓦罗并且认为在不太肥沃的土地上(gravia loca)用雇工比用奴隶更有利。因此,至少在瓦罗《论农业》的语境下,似乎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并不是当时的普遍分类法,而且农田上的劳力既包括奴隶也包括自由民出身的雇工。
奴隶与劳作的关系、奴隶人口数量统计、奴隶童工、奴隶姓名研究,以及奴隶史料汇编等研究专题和领域在过去40年间获得长足进展。波德尔(John Bodel)对“奴隶劳动”(slave labor)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几乎没有专门属于奴隶的“劳动”,自由民与奴隶的职业分工基本相同。除了服兵役、从政、法庭辩护等之外,很难说有什么工种或职业是仅限于自由民而将奴隶排除在外的。克里斯蒂安·拉埃斯(Christian Laes)首次对古罗马时代的奴隶童工进行系统性的考察,展示了法律、铭文、纸草文书、考古资料中关于售卖购买婴儿与幼童的资料,以及非常年幼的工匠及娱乐行业男女童奴的信息;沃尔特·谢德尔(Walter Scheidel)对罗马共和时期的奴隶供应以及帝国时期意大利、埃及和其他地区自由民与奴隶人口数量进行了量化评估,比如帝国时期意大利城市自由民约130万,乡村自由民人口350万,而城市和乡村的奴隶人数各约60万,相比而言,埃及的奴隶人数不到意大利的三分之一;索林(Heikii Solin)分类统计罗马的奴隶名字,指出有些名字在奴隶名字中特别普遍,比如Felix(“幸运的”)、Eros(“爱”)等等。不过希腊名并不代表该奴隶来源于希腊,在奴隶名字中,希腊名相当普遍。
刘津瑜认为,这些最新研究的一些推动力和源头可追溯到1980年代前后。当时出版的一系列论著如基斯·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的《征服者与奴隶》(1978)、摩西·芬利(M.I.Finley)的《古代奴隶制与现代意识形态》(1980)和奥兰多·帕特森(Olando Patterson)的《奴隶制与社会性死亡:一项比较研究》(1982)具有重要意义,开辟了奴隶制研究的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路径,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发展方向。
奴隶制社会研究的首要问题是何谓奴隶?何谓“奴隶社会”?摩西·芬利和大多数学者主张根据财产关系界定奴隶和奴隶制。“奴隶”是一种被永久占有的“财产”,奴隶制体现了主人对奴隶的私有关系。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称之为“非人的束缚/奴役”(inhuman bondage)。在芬利看来,“有奴隶的社会”不一定是“奴隶社会”,只有当私有土地、奴隶人口和剩余劳动生产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奴隶社会。基斯·霍普金斯、芬利等都认为,迄今为止只有五个奴隶社会。
不过,并非所有史学家都赞同芬利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只要为精英阶层提供剩余产品的主要劳动者为奴隶就可称为“奴隶社会”。社会学家出身的帕特森对66个“有奴隶的”社会进行概括,认为“奴隶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奴隶的“社会性死亡”(social death)。这又有“侵入式”(intrusive)和“排挤式”(extrusive)两种方式。奴隶被视为由外侵入的敌人、无父、无国、无宗教,他们被排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不被当人看待,被剥夺了为人的权利,他们丧失了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奴隶的婚姻关系和亲属关系不被法律所承认。因此,沦为奴隶就相当于“社会性死亡”。
“社会性死亡”这种说法在受到学界认可的同时,也遭到许多历史学家的批评,认为它完全脱离历史语境,是一个“蒸馏”出来的抽象概念,不能准确反映奴隶的切身经历和实际生活。比如,文森特·布朗(Vincent Brown)强调美洲奴隶制下的奴隶们不仅能保留原先的文化,还能进行反抗。约瑟夫·米勒(Joseph Miller)在其2012年的专著《奴隶制作为历史的问题: 全球化角度》(The Problem of Slavery as History : A Global Approach)认为“社会性死亡”是个“去语境化的”主人-奴隶二元构建。就罗马史而言,学者们也从奴隶的“家庭”与“婚姻”、奴隶的反抗、奴隶解放等资料出发对“社会性死亡”提出了质疑。比如,波德尔(Bodel)强调在罗马时代,奴隶在法律上只是一种暂时性身份,“奴隶解放”标志着社会性死亡的终结,在新世界的复活与重生。这场争论反映了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冲突,历史学家强调必须在历史语境下开展奴隶制研究。哈珀(Kyle Harper)甚至在《晚期罗马世界的奴隶制,公元275-425年》(2016年)中称“社会性死亡”纯属想象(imaginary)。
奴隶制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罗马人为什么使用奴隶,而不更多地使用自由人劳动?基斯·霍普金斯指出奴隶价格并不低廉,再加上维持奴隶生存的支出,整体成本不低,而奴隶又未必积极干活,那么奴隶制的经济逻辑在哪里呢?他的回答是,奴隶不需要像公民一样被征兵打仗,奴隶主可以强迫他们超时工作。奴隶制也使得奴隶主可在售卖土地的时候附带足够的劳力。更重要的是,在奴隶制下,可组织奴隶进行协作劳动,成为组织劳力的方式。而土地拥有方式的突变也是一个因素,大土地意味着和小农经济完全不一样的经济规模。罗马的征服使得上层拥有大量的财富,但投资机会不足,自由劳动力短缺,而奴隶制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式。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即罗马公民拥有政治权利(比如作为投票人),这限制了上层系统剥削他们的可能性和程度。所以奴隶制满足了征服扩张中罗马社会的需求,富裕的罗马人能通过剥削“外人”享受征服战争的成果。此外,成为奴隶主也是一种身份象征。沃尔特·谢德尔(Walter Scheidel)同意霍普金斯、芬利的说法,他认为真正的奴隶制经济在古代世界十分罕见。比较典型、真正遍布生产领域的奴隶经济可能只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意大利腹地存在。谢德尔在《希腊罗马世界奴隶制的比较经济学》(2011年)一文中对霍普金斯和芬利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细化,把奴隶制经济置于古希腊罗马经济活动的特征、激励体制、价值体系和自由民的职责等变量下进行考量。他指出奴隶制能够持续,是因为可以起到减少劳力的流动成本,降低人力资本流失的功能。另外,奴隶制可以解决劳力匮乏问题,而劳力之所以匮乏或昂贵,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对于古希腊罗马城邦来说,公民的政治、军事参与度高,并且公民/外邦人的区分较为显著,在这样的体制下,发展奴隶制的可能性更高。奴隶制的持续还需取决于奴隶供应。谢德尔一直研究奴隶来源问题,共和时代中后期战俘是奴隶的主要来源这一点极少有人质疑,罗马帝国时代的奴隶来源则争议较多。90年代,谢德尔认为罗马帝国时代奴隶主要来源于家生子,占比80%。但后来他将多种变量纳入研究,特别是奴隶的健康状况与疾病、奴隶人口中男女性别比率不均、奴隶的预期寿命、奴隶家庭的不稳定性、奴隶获得解放的年龄等等。2011年时,谢德尔进一步明确:奴隶再生产可能占帝国时代奴隶来源的50%,其余来自奴隶贸易、弃婴,等等。
奴隶通过何种形式反抗奴隶制?研究表明古代世界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比较少见,并且主要集中在共和时代后期。奴隶往往采取逃跑、怠工、“虐待”小主人和书写等“微反抗”形式。萨拉·福斯代克(Sara Forsdyke)2012年的专著《奴隶讲故事》一书考察奴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借用政治学家的理论,指出这些故事创造一个与主流政治空间相区别的文化空间,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例如,《伊索寓言》就是通过塑造一个个充满魔法和权力颠倒的世界,实现奴隶的精神宣泄和心理复仇,可以通过分析这些寓言的“表面文本”和“隐藏文本”以及两者之间的言说来深挖它们的意义。
被释奴研究的新进展体现在介于自由与奴役之间的身份研究和罗马帝国的被释奴文化研究。古罗马的奴隶可能被多位主人共同占有,被某个主人解放,成为自由人,但在另一个主人那里仍是奴隶,以至于在同一人身上存在不同的自由和奴役比例。文学作品中被释奴的形象反映了罗马上层读者群对被释奴文化的共同理解。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笔下的被释奴暴发户特利马尔齐奥(Trimalchio)的形象比较戏谑化,是受到嘲弄和讽刺的对象。不过,贺拉斯在诗中赋予其被释奴父亲以正面形象,赞美他的勤俭与节制,不依靠出身,凭借德行提升社会地位,而这种美德恰好符合共和国末期新的意识形态,即公民的自由应当是“有节制的自由”。
报告结束后,刘津瑜教授与线上学者、学生进行了进一步交流和讨论,并进一步梳理了关于古罗马奴隶解放的频率、解放奴隶的原因(奴隶主解放奴隶并非做慈善,各有其目的,而且被释奴仍然要对原主人负有义务)、帝国时代的奴隶来源(奴隶再生产、奴隶贸易、弃婴、战俘等),以及被释奴与前主人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布莱德利(Keith Bradley)与穆瑞森(Henrik Mouritsen)的研究,后者认为被释奴与前主人之间在经济上(比如资金方面)和社会关系上都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本次活动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承办,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较研究中心、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登峰计划”2022年系列讲座第六讲。
(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 胡玉娟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