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号 :[大] [中][小]
打印
黄艳红评《司法与王权》︱旧制度政治生态的诊断书
2020-07-15
(来源:澎湃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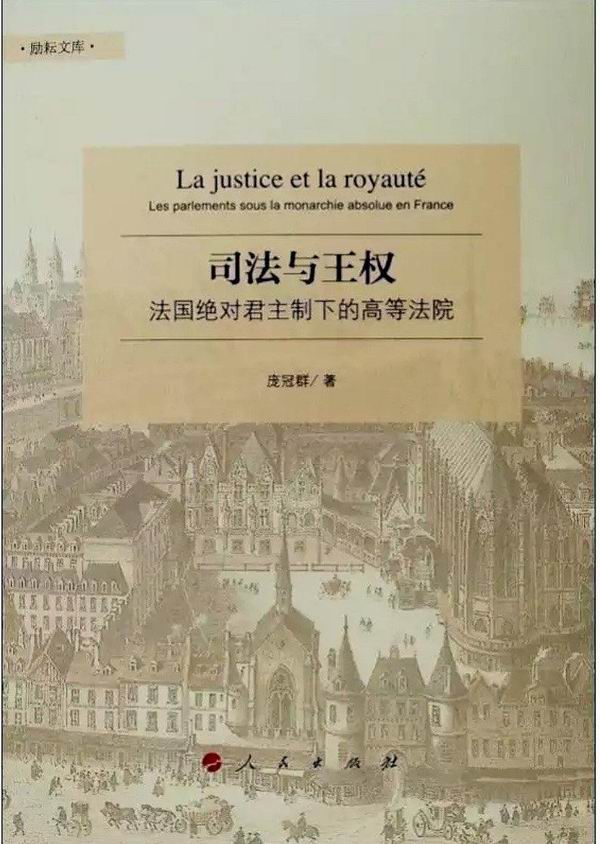
《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高等法院》
庞冠群著
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278页,55.00元
法国大革命“主要是一场带有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带有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这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学者乔治·泰勒(George V. Taylor)的一个论断。当代的研究者,不管是否赞同泰勒的论断,都已经不再仅仅从社会经济演变的角度去分析这场革命,尤其是它的起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政治文化研究一度成为法国革命史研究的主流,随之带动了对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史的重新考察。对国际学界的这一动向,我国学界对此已有关注和回应,近期北京师范大学庞冠群教授的新著《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高等法院》(以下简称庞著)则为这个领域平添了一份厚实的成果。
一
在今天,熟悉法国旧制度的读者都了解,在旧制度的最后半个多世纪中,高等法院(Parlements),尤其是巴黎高等法院与王权的矛盾是政治生活中最主要的话题之一,甚至可以说是诱发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对于这个重要历史角色的看法,各家却有很大的分歧。庞著开篇对高等法院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详尽的回顾。不过,与一般的学术史的写法不同,作者始终把学术发展和学术观点,与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和思想演变结合起来考察,并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见解。且以第二帝国时期对高等法院的评判为例。从政治逻辑上说,拿破仑三世应该不会喜欢制约君主权威的高等法院,但他上台之初设立元老院时,竟将这个机构比作旧制度时代的高等法院。对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庞著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这是独裁者为自己寻找一件法治的外衣,这个姿态影响了对高等法院的研究。这个片段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学术难以摆脱政治的影响,但两者的关系是多样和复杂的。
从庞著的分析来看,拿破仑三世的立场在十九世纪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大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中,高等法院在旧制度末期与王权的对抗,经常被认为带有捍卫公益、维护法制的积极意义。但十九世纪也为二十世纪对高等法院的严厉批判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约瑟夫·德罗兹(Joseph Droz)的著作。对高等法院历史角色的看法,与关于大革命的起因和旧君主制的命运的见解关系最为密切,庞著则以1770年代的莫普改革为核心,突出了这种关联性。德罗兹认为高等法院的抵制纯粹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团体利益,而莫普改革本来有可能粉碎这个贵族集团的不良影响。改革阻挠者的形象成为二十世纪法国史学中的主流。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法国史学界的左右两翼竟然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作者在这里指出了两派不同的出发点,但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合流,或许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丰富了我们对托克维尔论点的认知。旧君主制的辩护者和革命的辩护者,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国家主义者,相信国家主导的政治革新是进步的原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旧制度和大革命是连续的。
随着二十世纪后期英美学者的介入,这种立场鲜明的史学开始向侧重时局理解的研究转变。在笔者看来,庞著分析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以朱利安·斯旺(Julian Swan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检讨此前研究者概念工具中的时代误植问题,他们尤其强调应回到旧制度的制度逻辑和政治语境之中,理解事态发展的动力和性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关于高等法院进步与反动的二元对立判断。英美“旁观者”的介入给法国史研究带来的新气象,是值得深究的现象。大约在朱利安·斯旺等人介入高等法院研究的同时,在中世纪史研究领域,英美学者对公元千年之际的封建变革论的修正,看来有某种相似性。论者指出,他们与现代法国政治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不同,没有那种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色彩,能够更为平衡地看待国家与其他历史角色之间的关系。或许正因为这一点,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研究者的交流才更有必要。
二
幸运的是,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庞著可以更为公允地博采众家之长,从作者所称的“多重路径”来考察高等法院在旧制度时代的角色演变。全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高等法院在绝对君主制中的制度性地位的分析,二是以莫普改革这一事件为中心,分析高等法院与旧制度末期政治文化演变的关系。在我看来,前者是后者的必要铺垫,两者共同构成旧制度的政治生态的“深描”式剖析。
如前所述,关于高等法院,尤其是巴黎高等法院的研究,与绝对君主制和法国大革命的起因问题密不可分,因此高等法院与王权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心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同样是庞著关注的重点,但它首先对高等法院的发展史做了一个长时段的追溯,其研究旨趣大大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史,融入了图像研究、法制史和公共舆论分析。对于国际学界的经典和前沿研究,庞著亦有充分的关照和吸收。作为王国的主要政治机构,高等法院与王权的关系不仅体现在谏诤权、法律注册权等“基本法”层面上,也反映在各种政治性仪式中。受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的影响,西方学界对法国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所谓四大君主仪式进行过认真探讨:加冕礼、葬礼、入城式和司法床(lit de justice,庞著意译为“御临法院”)。而在庞著中,除了入城式,上述经典研究均有涉及,尤其是与高等法院有直接关系的司法床仪式。不过作者强调,司法床,乃至“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意义,是不断被转写和重新阐发的,它的意义随国王和高等法院关系的演进而有所变化。法国学者雅克·勒维尔(Jacques Revel)在讨论这类君主制仪式时曾认为,不能对这类仪式进行宪法式的解读,它们的主要意义在于象征层面,而不是现代宪法意义上的法条式的规范。庞著关于司法床的分析,很好地展现了“仪式政治”的复杂面相。这种仪式当然有较为明确的象征意义,即国王是国家的第一法官,但它的声望和影响力、国王要在该仪式上达成的目的,以及它的人员构成,都是有变化的。
这种变动性不仅体现在象征层面上,而且体现在实际的制度发展中。在笔者看来,庞著在后一方面的分析意义更为重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从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出发,这就是“司法国家”和“行政国家”,它涉及近代早期政治发展的关键事实。作为主权的持有者,国王同时具有骑士和法官两种身份,这体现在加冕礼上的信物中,即庞著提到的正义之手和马刺等信物。这些都让人想起中世纪以来国王作为“和平”与“正义”维护者的角色。但在君主制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国王作为最高法官和“正义之源”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正如约瑟夫·斯特雷耶等人指出的,王国政府机构的发展,首先出现在司法领域,高等法院在其中无疑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不过庞著的分析提醒我们,不能以现代政治生活中职能明确、权责明晰的条理化思维去理解旧制度时代的政治机构。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尤其值得关注。中国很早就发展出成熟完备的官僚制,相比而言旧制度的官僚制可能具有更为明显的持续变异的特征,并给我们的理解和研究造成很大的挑战。
庞著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高等法院承担的社会治理职责。仅这个事实本身就值得思考。按现代人的理解,高等法院应该是个纯粹的司法机构,但实际上它也承担广泛的行政管理职能。作者指出,这个司法机构从一开始就行使所谓“总治理”(police générale)的权力,尤其是涉及城市民生和救助贫病的责任。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人们习惯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分,在旧制度时期可能并不明确;在君主制发展的早期,法庭往往兼理民政,这是“司法国家”的特征。但是,这种体制不能很好地适应君主制国家的内外政策。这不仅因为法庭行动迟缓,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因为法官的职位日益成为一种世袭的家产。面对这种局面,国王开始任命直接听命于他、可以随时撤换的官员进行治理,这就是“行政国家”兴起的背景。对绝对君主制的制度史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司法国家和行政管家的并存,以及两者之间持续不断的争吵。这种情形在旧制度最后一个世纪的税收体制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各级法庭总是指责国王直接派遣的官员(即行政国家的代表)侵夺了它们在税收监管方面的传统权利。庞著对类似现象有一个总结性的评论:路易十四已经开始剥离高等法院的行政权,使其成为一个更专业化的司法机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看来它佐证了托克维尔的论点:是拿破仑完成了路易十四未竟的事业,帝国时代省长的前身就是革命前的Intendants(地方行政官),行政权主导了地方治理。而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可否认为是大革命和帝国实现了司法与行政的分化呢?
司法国家与行政国家的冲突,同样反映在舆论和意识形态论战中,对此庞著做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尤其是在莫普改革期间。在进入旧制度的这最后一幕政治大戏之前,应该循着庞著的思路讨论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制度演变的特征。
莫普晚年在陈述自己的改革意愿时说,他想重建社会链条的各个环节,在他看来,君主制的传统足以赋予国王重组社会链条的权力。莫普的这个说法,让人联想起1776年高等法院在反对杜尔哥改革时的另一个比喻。法官们对旧制度的团体社会做了这样的定义:“团体像是一个巨大链条上的各个环节,而这首要的环节就在陛下您的手中,您是……所有环节的首脑和最高管理者……单是摧毁这一珍贵链条的想法就是极端可怕的。”如果笔者的理解没有错,庞著中马尔泽尔布关于法国“基本法”的认知,应该接近于后一种链条意象,而且,两种意象都试图从历史中寻找依据。它们的区别究竟何在?这里可以参考基思·贝克(Keith M. Baker)的看法。他认为,绝对君主制从其诞生之初就有其法律和制度前提,它必须维护历史形成的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各种特权为表征的权力关系格局。当博丹提出主权论的时候,正是为了挽救和维护这种格局和条件。但是,当王权完成了这个使命、当它的抱负开始扩展时,这个格局和条件逐渐成了一种束缚。它要重组、要挣脱团体社会的“链条”。于是国王不再是链条上的一个构成环节、不再是从内部维持其运转,而是凌驾于其上,要对它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切除和重构——莫普就是这样的操刀手。但在司法国家的链条意象中,国王的做法完全破坏了整个制度和法律基础。因此我们回到了丹尼斯·里歇(Denis Richet)的那个著名论点:绝对君主制越是自我强化,它就越是在摧毁自己的合法性基础。
在这一政治史和制度史的背景之下,庞著关于绝对主义理论的辨析、关于莫普和马尔泽尔布之间意识形态之争的阐发,就有了重要的解释价值。绝对主义理论从来不认为国王可以逾越神法、自然法和法国的基本法;但另一方面,绝对主义这个概念本身似乎又意味着国王享有完全的立法权,而王权的代表者强调的正是这个侧面,前述“王在链条中”与“王在链条上”大概就是对绝对主义两种理解的反映——而这两种理解可以在司法国家和行政国家中找到制度化的表达。
三
庞著的第二部分是有关莫普改革的事件史剖析。记得作者曾希望以戴尔·范克雷(Dale Van Kley)讲述1757年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达米安案与旧制度的解体》,1984)的方式来讲述莫普改革,而著作的标题似乎也在做这样的提示:“革命的预演:莫普改革与绝对君主制的解体”。这大概接近于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所称的“结构-事件研究”。在我看来,著作对这个事件的呈现角度之丰富,足以视为结构-事件研究的楷模。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政治—制度发展史中的莫普改革,还有舆论场中的莫普改革,观念与话语嬗递中的莫普改革,以及宫廷阴谋和社交网络中的莫普改革。
庞著第一部分的政治史和制度史铺陈足以表明,1771年司法大臣莫普取缔高等法院、按自己的意志重组高等司法系统,可以视为王权和行政国家对司法国家的一次清算,或者一场“政变”。但是这个事件之所以会在旧制度末期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轩然大波,离不开当时法国的政治生态,正是这种生态使得这场冲突在各个领域内加速发酵,并成为孕育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具有结构性转折意义的事件。
莫普改革的出现,从其直接原因来说,是司法机构与国王的矛盾不断升级的结果。作者指出,1750年代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代,这不仅仅是因为税收和宗教问题加剧了高等法院与王权的对抗,而且这个时候产生了新的观念和思想资源。在这里,读者便可理解为何作者会对冉森主义进行长篇追述:到1750年代,这场冲突导致的思想论辩和舆论战,形成了高等法院独特的意识形态:高等法院的理论家们认为,这个机构从国王的代表演变成了民族的代表,国王与民族剥离了;在作者的论述中,这个思想转变可以视为宗教争议的政治外溢效应,因为以教会公会议至上原则来对抗教皇,与民族及其代表机构来对抗王权,两者存在明显的平行关系。当然,在法院贵族的意识形态中,他们就是民族的天然代表。
冉森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从人员和组织上说,他们构成一个连接高等法院、律师界和舆论出版界的网络;而且,作为反莫普改革的中坚,这些作者宣扬一种毫不妥协、严肃克己的牺牲精神——这不禁让人想起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精神气质;庞著进一步指出,莫普改革期间崭露头角的律师们,将对大革命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说冉森主义仍对这个群体具有影响力,可以肯定地说它从心态和情感方面给大革命打下了烙印。
对冉森派网络的仔细梳理,展现了作者对当时政治生态的精准把握。更有意义的是对其中的演变的分析。在耶稣会被驱逐后,冉森派斗争目标的转变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个转变对莫普改革的舆论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样地,作为一个具有结构转折意义的事件,莫普改革给法国政治生活造成的另一个深远影响,是高等法院影响力的衰退,它丧失了莫普改革之前作为“民族代表”的抱负,而三级会议作为民族代表的言论,顺理成章地日益凸显出来。
关于莫普改革的实施过程和失败的原因,庞著都有相当精细的剖析,从宫廷政治到法官们的立场选择。就我的阅读体会来说,作者关于莫普改革的分析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政治话语、或曰政治修辞术的嬗变。作者在论述莫普改革引发的舆论战、莫普与马尔泽尔布的改革之争时,资料的运用和分析都很充分,开掘的问题也很多。从各方的论证策略来看,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以历史传统来证明自己诉求的合理性,无论是莫普还是马尔泽尔布,无论是高等法院的理论家勒佩日,还是布列塔尼事件中抨击司法贵族的总督达吉永,他们要么援引法国的过去作为其政治诉求的依据,要么抨击对手违反历史中形成的“基本法”。看来这是一种十分普遍、可能也十分古老的政治修辞术。庞著在分析莫罗和勒佩日的论证策略时,指出了君主制的法兰克起源与罗马起源背后的政治要害,这个争论在十六世纪后期宗教战争期间就已经有了明确的展现。诚如作者所言,这些争论牵涉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对“基本法”理解,论战各方都是各执一词。但重要的是作者的这一看法:莫普改革中的对立双方在攻击对方践踏根本法、不尊重历史传统的同时,却把基本法和历史传统的内涵掏空了。如果引申一步,历史——或想象的过去——作为一种论据看来无法为当时的政治僵局找到出路。从这个角度看,从勒佩日到纪尧姆-约瑟夫·塞日之间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法国政治话语中的修辞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从言说历史到谈论契约和公意——而契约和公意是超历史的。作者也明确提到,塞日离西耶斯只有一步之遥;1788年,当圣埃蒂安—拉博公开宣称“我们的历史不是我们的法典”时,这个转变看来最终完成了:政治的使命不再是恢复和延续(想象中的)过去,而是要彻底推倒过去。
基思·贝克曾说,作为一场政治文化变革,法国大革命用自己的一套话语重新定义了集体生活。1789年的革命者“天赋人权”来为新时代立法,二十年前的法国人却在历史中搜寻政治生活的依据。庞著对于莫普改革的政治生态的深描,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揭示这个政治事件是如何成为催生现代政治文化的酵母的。如果说读后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旧制度的司法体制和政治文化与大革命和帝国时代的历史的比照和勾连还不够系统,如果能进一步完善,可能更有利于揭示旧制度的时代特征与法国大革命在现代世界史中的转折性意义。
(黄艳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