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百亮:从情感史的视角看流行病
2021-02-05
(来源:《文汇报》2021年2月4日第9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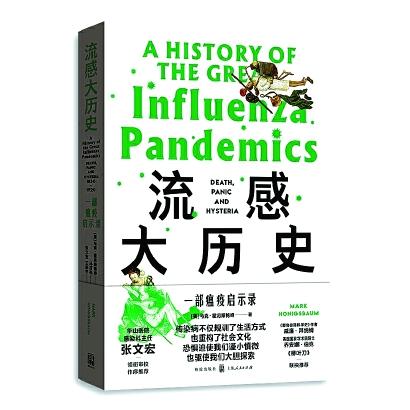
马克·霍尼斯鲍姆 著 马百亮 译 张文宏 王新宇 校 《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格致出版社,2021)
“一定要和这封信保持距离!看完了一定要消毒。我们营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和大约30名军官都感染了西班牙流感。周五,医院里人满为患,体育馆的临时医院也爆满,现在到处都是裹着毯子缩成一团的人……年轻的士兵们像苍蝇一样纷纷病倒。”
1918年6月24日,在斯卡伯勒附近狂风肆虐的战场上,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爬进帐篷,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便是信的开头。乍看之下,欧文似乎非常谨慎,甚至有些惊慌,但是读到后面,会明白这是对当时英国人对待“西班牙流感”的典型态度的嘲讽和揶揄,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显然是在逗母亲开心。他接着说:“这种事情太司空见惯了,我是不会这样大惊小怪的。我已经决定不这么做了。”可见,他根本就没有认真对待消毒措施,反而认为流感是个笑话。
这是《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中众多与流感疫情有关的趣闻轶事之一。本书作者是英国著名调查记者和医学史家马克·霍尼斯鲍姆。他本是伦敦大学城市学院的高级讲师,在《观察家报》《柳叶刀》和《医学史》等大众和专业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撰有多部医学史著作。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也让他变得“炙手可热”,或讲座,或访谈,或撰文,或书评,获得邀约不断。截止到目前,他的作品《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和《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都已被译成中文。
《人类大瘟疫》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遭受的几场全球性流行病,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西班牙流感、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也包括不那么众所周知的如20世纪20年代的洛杉矶鼠疫和30年代的鹦鹉热。在这部书中,霍尼斯鲍姆详细介绍了这些流行病暴发的经过,揭示了包括城市化和全球化在内的人类行为是怎样影响流行病的传播方式,赞扬了作为病毒猎手的流行病学家克服地方、国家乃至全球的机构性障碍,以非凡的勇气和决心追查疾病的源头,并提醒人们“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流行病是否会出现,而在于何时出现”。这本书第一版问世于2019年4月,就在半年后,新冠疫情暴发,可谓一语成谶,而我们至今依然生活在这场疫情之中。霍尼斯鲍姆在书中一再警告说,瘟疫的到来不可预测,总是会让人类措手不及,而在2020年3月底,他本人也出现了发烧和咳嗽的症状,因为当时没有接受核酸测试,无法完全证实,但他患上的很可能就是新冠肺炎。
这本书第一版的副标题是“100年的恐慌、歇斯底里和傲慢”,中文版也是据此版本翻译过来的。2020年6月,本书又出了第二版,增加有关新冠肺炎的章节,因此探讨的大瘟疫由原来的9个增加到了10个,副标题也相应改成了“从西班牙流感到新冠肺炎的全球传染史”。中文版2020年5月问世,由于时间差,很遗憾地没能把这一章包括进来。
中文版刚刚问世的另一部作品《流感大历史》虽然中文副标题是“一部瘟疫启示录”,但原作的副标题其实是“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这本书探讨的仅仅是流感,霍尼斯鲍姆在其中追溯了现代流感概念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从重感冒的同义词逐渐变成值得大众关注的科学谜题,并成为更广泛的“世纪末”焦虑和生物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因此,就像作者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这本书的三大支柱是传染病的医学史、最近的情感史学和物质文化社会学。霍尼斯鲍姆的这两本书尽管主题涵盖范围大小不同,副题却都包括“恐慌”和“歇斯底里”,他的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从情感反应的角度讲述流行病的历史。从2009年出版的《与恩扎一起生活》,到2014年的《流感大历史》,再到2019年的《人类大瘟疫》,随着霍尼斯鲍姆对于瘟疫叙事的驾驭能力越来越炉火纯青,探讨的话题也越来越广泛,但一以贯之的是情感叙事的写作风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作者对于史料的选用有关,其中包括报纸文章、文学作品、医生的私人记录,以及信件和日记。
就像张文宏教授在为《流感大历史》中文版所作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从古至今的人类历史始终是和传染病纠缠在一起的。一部传染病史,就是人类和各种微生物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观之,人类和微生物互动的历史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人类占上风,人与微生物相安无事,相得益彰,另一种是致病微生物占上风,这时就会造成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瘟疫和饥荒一样,已经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留下深深的创伤。因此,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历史学著作中,瘟疫叙事一般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疫情本身的描述,一是人们对疫情的思想和心理应对,尤其是情感反应。如果说前者因为具体瘟疫的不同而千差万别,那么后者则因为人性跨越时空的普遍性而大同小异。毕竟,瘟疫给人类带来的是病痛和死亡,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触动内心和情感呢?在这方面,无论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雅典瘟疫的描述,还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家乔万尼·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对中世纪佛罗伦萨瘟疫的书写,还是存在主义文学家阿尔贝·加缪虚构的鼠疫期间奥兰小城的故事,概莫能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我们看到的是瘟疫之中的人们对神圣和世俗之事都漠不关心,变得肆无忌惮。对他们来说,生死难料,荣誉和财富都如过眼云烟,于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沮丧之情笼罩着雅典,他们通过神谶寻求解释,并迁怒于领导人伯里克利。在《十日谈》中,人们把瘟疫归因于上天的恶作剧或是对人类邪恶的惩罚,变得恐惧和猜疑,他们远离瘟疫受害者,自行隔离,有节制地自得其乐,或是纵情享乐,挥霍无度。而在《鼠疫》中,加缪以更多的篇幅、更加文学化的手法描绘了瘟疫下的人生百态。
今天,情感史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从情感的角度考察瘟疫成为一个有趣且回报丰厚的尝试。如果说《人类大瘟疫》限于篇幅,对每一种瘟疫的介绍更就事论事,叙事更外在化和新闻化,《流感大历史》则更偏重对情感的描绘,叙事更为内在化和文学化。这也与流感症状的变化多端有关,这一特征赋予流感很强的隐喻灵活性,例如,它被喻为希腊神话中变幻莫测的海神普洛透斯,或是被喻为罗马神话中司掌大门和开端的两面神雅努斯,因为和两面神一样,流感也有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一张面孔与死亡和痛苦有关,西班牙流感经常被和黑死病相提并论,而另一张面孔出现在两次流行病暴发之间,因为此时的流感更多被视为一种不便,而不是致命的威胁,被认为和普通感冒一样微不足道。关于流感和普通感冒之间的区别,张文宏教授也有一个妙喻,那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猫和老虎,虽然都是猫科动物,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流感大历史》文学化的一面还体现在它多处对《鼠疫》或明显或隐含的借用,例如,在谈到死亡人数之多让人无法想象,成为抽象的数字,反而无法激起人们的情感时,作者直接引用了《鼠疫》中的一段话:“但死一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再如,他对于瘟疫的必然性和不可预测性的警告,让人们想起《鼠疫》的最后一段话:“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明镜在心: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贯穿全书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即流感除了本身具有的生物学性质之外,还吸收了社会、文化和史学的因素。例如,俄国流感来无影,去无踪,就像残忍的“开膛手杰克”一样阴森可怕,让伦敦人毛骨悚然。它突然神秘地降临,散播恐慌、歇斯底里和死亡,然后又同样神秘地消失。后来,随着流感日益成为科学关注的对象,它又开始被视为更加广泛的社会病态的晴雨表,而这些病态与维多利亚时代对疲劳、堕落和现代生活的技术化过程的担忧有关。电报技术、运输技术和统计学的发展,媒体和整个社会对名人患者的关注,以及当局和广告商对人们恐惧心理的利用,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人们的歇斯底里和恐慌。
霍尼斯鲍姆借鉴了福柯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理论,对百年前疫情暴发期间的恐惧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和阐释。在和平时期,像石炭酸烟丸这样的专利药品和保卫尔这样的保健品是利用人们的焦虑和恐惧进行营销,但在战争时期,这类商业广告开始用民族主义的话语来赞美恬淡寡欲和坚韧不拔的美德,使用像“抵抗”和“攻击”这样的军事隐喻和医学概念。这是因为,在和平时期,恐惧不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而在一战期间,恐惧被认为会削弱前线和后方的士气。为了团结国内一切力量对抗共同的敌人,英国政府在国内媒体的自愿合作下,有意识地培养对德国的仇恨情绪,而流感风险则被同样有意地忽视,也没有发起流行病学调查。然而,随着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的增加,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之上,为避免流感造成更严重的破坏,媒体、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恢复了以前强调流感风险的话语。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霍尼斯鲍姆指出,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迟迟不愿把新冠疫情升级为“大流行”,除了卫生和政治考量之外,另外一个因素是这个词在英语中的表达“pandemic”太容易让人联想到“恐慌”,因为其英文表达是“panic”,比“pandemic”仅少了三个字母而已。需要指出的是,其实这两个词的词源是不同的,后者和疾病一词的搭配出现于1853年,其词源构成和表示“传染病”的“epidemic”是一样的,“epi”和“pan”都表示“全体”,而另外一部分来自表示“人”的“demos”。而表示“恐慌”(尤其是指没有明显原因或由微不足道的原因及危险引起的夸张的恐惧)的“panic”一词才真正源于希腊神话中代表森林和田野的潘神,据说他会发出神秘的声音,而这种声音会在兽群或人群中引起具有传染性的、毫无根据的恐惧。
虽然可以说每一次疫情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暴发都让人类出乎意料、措手不及,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以往的暴发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今天阅读霍尼斯鲍姆对于一个世纪以来多场大流行的描述,我们总是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当前的新冠疫情而言,我们也总是在将其与之前的各种大流行相比较,例如SARS,因为两者的病原体都是冠状病毒。就像国际知名流行病学家罗伊·安德森在2004年指出的那样,那次成功战胜SARS病毒只是因为“侥幸”,因为其传染性很低,加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采取了十分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如家庭隔离和大规模隔离检疫。他还预测,如果SARS在北美或西欧暴发,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这里的人更喜欢诉诸法律。此外,他还指出,真正的全球威胁不是SARS病毒,而是一种具有全新抗原性变异的流感病毒。今天来读安德森的这篇文章,我们不得不佩服其先见之明。
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对抗瘟疫的历史也是一部情感的历史。安德森提醒我们,对SARS的有效控制可能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自满情绪,认为我们曾经成功过,因此还能再次成功,这样的情绪可能会蒙蔽人们的双眼,教人忽视真相。无论是在其著作中,还是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霍尼斯鲍姆也总是在发出这样的警示:人类行为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还会导致新的、未知病原体的出现和变异,而全球航空旅行的发展意味着病毒可以更快地传播,使流行病在72小时内变成大流行。人类应该规避任何关于知识和技术进步的幻觉和自以为是,因为一旦遇到新情况,曾经有效的方法往往会把流行病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媒体和政府导向错误的道路。而在为《流感大历史》所作序言的结论部分,张文宏教授也告诫我们:“微生物在进化,人类也在进化,每次流行都各有特点。人类必须保持谦卑之心,依靠科学,既要跑得比微生物更快,也要学会和微生物共生共存。”
(作者:马百亮,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